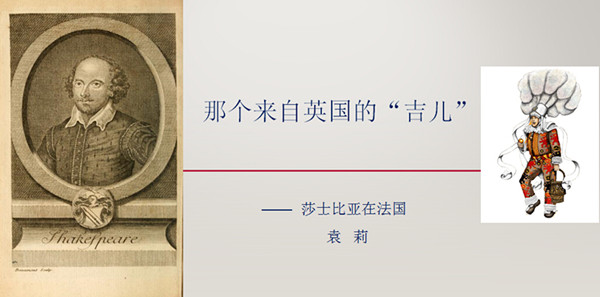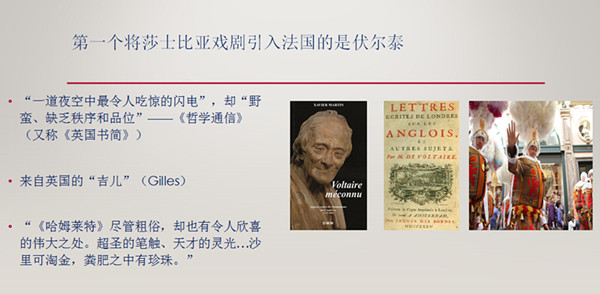莎士比亚在法国被认知与接受,是个艰难而缓慢的过程。在莎士比亚诞生之前,法国已经有了文艺复兴巨人拉伯雷,有了唤醒欧洲现代意识的思想大师蒙田,随后,法国文学完全笼罩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光芒之中,其伟岸与庄严铸就了古典主义的铜墙铁壁,完全遮蔽了邻国发生的一切。因此,在十八世纪之前的法国,对莎士比亚的名字鲜有所闻,路易十四皇家图书馆如今只能查到一册珍贵的莎剧folio对折版。当时最博学的人是皇家馆长尼古拉·克雷芒(Nicolas Clement),对英语也一窍不通,他曾跟国王提及此书“想必是美的、自然的”。1708年皇家《翰林报》(Le journal des savants)中只有一句话提到“莎士比亚是英国最著名的悲剧诗人”,除此,也并无其它的解读与介绍。显然,直到十八世纪初,莎士比亚在法国仍是籍籍无名、完全无人问津的。语言的障碍或许是一个原因,毕竟那时欧洲的外交语言和“文人共和国”(République des lettres)所通用的语言是法语,而不是英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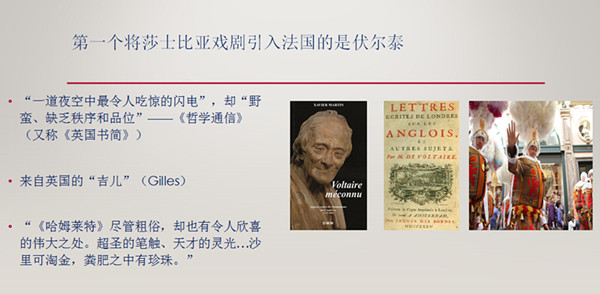
第一个将莎士比亚戏剧引入法国并促使其成功上演的人是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1726年,伏尔泰因得罪权贵流亡英国,偶然发现并读到莎士比亚,立刻惊为天人。这甚至成为了影响他创作生涯的一个大事件。在1734年发表的《哲学通信》中伏尔泰写道:“这是一道夜空中最令人吃惊的闪光。”他将莎士比亚比作是“英国的高乃依”:“不容置疑,他的天才具有强大的力量,异常丰富,自然又神圣,尽管缺少优雅的品味,也不太合戏剧的规矩。”十八世纪的法国剧坛仍是古典主义“三一律”的天下,伏尔泰认为这道闪电虽令人吃惊,却野蛮无比、缺乏秩序和品味。伏尔泰是路易十四时代古典文化的狂热拥趸,法兰西一切的文学形式在这个时代都是臻于完美的。他同意批评家布瓦洛的观点:“文学创作就应该是将自然轻轻遮上一层面纱。”他认为莎士比亚在舞台上直接表现流血的身躯、杀戮的场景,将“改变一个民族的品位,使观众们的厌恶强扭为愉悦”。相比于法兰西古典式的优雅,承蒙伏尔泰的恩赐,莎士比亚在法国便有了一个“吉儿”(Gilles)的绰号。吉儿,意指法国外省市镇上小剧场的闹剧演员,是庸俗和夸张的代名词。在伏尔泰看来,乡下闹剧演员“吉儿”们的对白,都比莎翁笔下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说的话体面。1748年伏尔泰写过一篇《论(古典与现代)悲剧》,明显带有偏狭的民族主义式的抵制情绪:“《裘力斯·恺撒》中屠戮的场景,《麦克白》中的守门人,《哈姆雷特》中的掘墓人,这一切都与当时的法国风俗格格不入,是超越古典戏剧三一律的‘非理性因子’,理应被查禁。语言上无异是野蛮的‘闹剧’,比如一部戏中竟出现两个‘疯子’,喝酒、唱歌、打斗、杀伐、吵骂……”在伏尔泰看来,市井生活中的普通人、社会阶层的混合、语言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相混杂,均不符合悲剧的品位和规则。
伏尔泰在法国古典主义传统与耳目一新的莎剧之间受到拉锯般的折磨。是讨好观众,还是革新、破陈,要魅惑还是激怒,因为魅惑一部分观众的同时势必也将激怒另一部分……伏尔泰自己也承认阅读莎士比亚为他带来了不少灵感和创新动力,他尤其推崇《裘力斯·恺撒》,亲自操刀翻译了这部剧,并受其启发写出了自己的《恺撒之死》。甚至后来有学者朗布里(Lounsbury)在一篇论文《莎士比亚与伏尔泰》(1902)中提出,伏尔泰的悲剧作品《扎伊尔》亦步亦趋地模仿了《奥赛罗》。有关伏尔泰抄袭模仿莎士比亚的争议在十八世纪晚期达到高峰,后来有法国学者杜伯图(Dubedout)特地撰文表达“不敢苟同”,专门替伏尔泰辩护。但不可否认的是,伏尔泰一方面深深地被莎士比亚的艺术吸引,另一方面却又拼命地批评丑化他,个中缘由相当耐人寻味。1736年《恺撒之死》的出版前言中,编辑在伏尔泰的授意下写下这样一段按语:“莎士比亚是英国的悲剧之父,也是这个蛮荒国土里盛行的野蛮文明之父。他高超的天才创造,既无文化也无品位,给欧洲戏剧界带来了一阵混乱。但其魔鬼般的文字,也不失自然杰作的部分。”
竭尽讽刺之外伏尔泰也有另一番良心表达(1776年致达尔让答的信):“《哈姆雷特》尽管粗俗,却也有令人欣喜的伟大之处。超圣的笔触、天才的灵光,从笔尖自然流露。沙里可淘金,粪肥之中有珍珠。”可以看出伏尔泰对莎剧种种刻薄的指责之中确有对美的由衷赞赏,“吉儿”的称呼虽夸张,却具备魔鬼般的吸引力。特别是当听说有人正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时,伏尔泰感受到了法国读者对海峡彼岸这位魅惑之王越来越浓的兴趣。戏剧观念保守的伏尔泰无疑是预感到了危险的临近,他在写给法兰西学院秘书达朗贝的信中说:“英国的‘吉儿’大有取代高乃依和拉辛的态势。” 事实证明,这一态势已势不可挡。
十八世纪莎士比亚戏剧在法国的早期译介是间接而变形的,任由译者为达成自己的戏剧主张和理念而随意更改原文。1730年伏尔泰将莎士比亚的五幕剧《裘力斯·恺撒》翻译改编成了《布鲁图斯》(Brutus),在法兰西喜剧院成功上演。对于《哈姆雷特》的独白段落,伏尔泰也做了很大的调整,他讽刺原文中的丹麦王子的话语“犹如外省集市上逗人笑的‘吉儿’小丑在聒噪……”伏尔泰拿着自己的尺子,随意删减、改编情节,诗行基本固定,采用亚历山大体,给韵也是传统法国式的,足以让人明显看出英法两套戏路的截然不同。
1745年, 拉布拉斯(La Place)为法国人提供了一个远比伏尔泰尊重原著的《哈姆雷特》“真正的译本”,但是与法国同时代出版的戏剧作品相比,该译本以散文体形式出现,在法国人眼里仍显得怪异、不合常规。但是莎翁剧中丰富的想象、多变的情节,却让法国人大开眼界。从此,法国人对英国及其文学的兴趣开始提升,英国文学开始在法国风行,特别是后来竟成为批评本国文学的一杆标尺。莎士比亚戏剧达到了巴洛克戏剧风格的顶点,以极其简约的方式创造出多重效果,而法国古典戏剧直至十八世纪中期,仍只呈现出很单一的写作程式。1769年,杜西斯(Jean-Francois Ducis)出版了法国第三个《哈姆雷特》的译本。杜西斯和中国早期的小说译者林纾一样,不识英文,几乎是根据伏尔泰和拉布拉斯的译文,“撰写”了这出“仿英悲剧”。他将哈姆雷特与鬼魂相遇的一段、奥菲丽亚变疯的一段尽可能缩减,并彻底重写了掘墓人的一幕,但今天的文学界不能否认,杜西斯的译本曾是当时的欧洲人,甚至拉美地区的读者发现莎士比亚的必经之路。
1776年至1783年,第一部莎士比亚全集(二十卷)由勒图尔纳(Pierre le Tourneur)在法国翻译完成并出版。与伏尔泰故意夸大莎士比亚语汇的粗鄙不同,勒图尔纳悄悄对台词中一些粗鄙极端的语汇加以改造,以免刺激、震动当时的法国文坛。译本的文字风格更细腻和缓,省略了双关语和文字游戏,删除了淫秽的用词,比如将“野鼠”改成“小偷”,“小家鼠”改成“昆虫”,“老鼹鼠”改成“隐蔽的幽灵”,“烂货”改成“坏毛病”。十九世纪的大文豪雨果曾评价说勒图尔纳的译本“只不过忙着掩饰莎翁的锋利,将其磨去棱角,熨烫平整”。也的确如此,拉布拉斯、杜西斯、勒图尔纳这些译者都可谓是高明的“熨烫工”、文化的中间人,目的是让莎士比亚能尽快地为法国读者所接受。勒图尔纳在译本序言中说:“莎士比亚的进入,给法国文坛的风景带来了一场进步的变化。莎士比亚比高乃依和拉辛都高明,古典主义的三一律戏剧过于呆板和迂腐。”然而长寿的伏尔泰看到这篇序言,很不以为然,尤其是“抄袭莎士比亚”的传言给他的文学成就蒙上了一层阴影,便更变本加厉地批判莎士比亚。
拉布拉斯和图尔纳的莎剧译本在法国文坛大获成功,在法国戏剧舞台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是否可以任由莎士比亚占领法国?拉芒什海峡另一侧吹来的文艺复兴的清风,直接在法兰西大地上制造了十九世纪初浪漫派的登场。这阵由莎士比亚为法国浪漫主义新一代带来的自由的狂风,之前曾长期蛰伏在“亚历山大体的暴政”脚下,与后大革命时代的布尔乔亚体制同时发生。法国人在莎翁的天才巨篆之下,能找出的不光是文化启蒙,还有真正的政治表达。
浪漫主义的奠基人夏多布里昂在他1801年的随笔中曾引用莎剧中一些美妙的片段,并兴奋地感叹:“若感受不到这些对话里的妙处是多么可怜!自然本身胜于情节,多简明,多直接!生活里多么真实的矛盾!所有的语言、社会阶层、戏剧场景如此接近,多好!” 莎士比亚是文学现代观念的标志,他在法国的命运,从此与浪漫主义运动密不可分。1810年,斯塔尔夫人主张法国文学“应该挣脱古典主义的束缚,虽然莎士比亚的北欧血统让他偏好暴力和粗犷的主题,但他的作品能够触及人心、煽动激情,所创造的戏剧效果逼真得如同现实世界”。但是斯塔尔夫人也期待法文译本对莎剧能有一定程度的改写,以期更加适应法国舞台,比如语句的繁琐、无用的重复、过多借用幻觉、有时又夸张过头、人物形象不够协调等等。在《论德意志》一文中,她指出莎剧之美的发现足以给法国文坛重新注满生机。
1821年古依佐(Guizot)出版了新的《莎士比亚全集》,使得以雨果为首的法国浪漫派年轻一代得以一睹莎士比亚的全貌。雨果是这样回应一个世纪之前伏尔泰这位启蒙思想巨人的嘲讽的:“‘吉儿·莎士比亚’,我之所以要这样称呼,是因为我既欣赏‘吉儿’,也膜拜莎翁。那个所谓的‘优雅’病,莎翁从未得过。”
早在1864年写作《威廉·莎士比亚》之前,雨果就对盛行于法国文坛的所谓品位和繁文缛节十分不以为然。在《威廉·莎士比亚》一文中,雨果用反讽的语气批评旧体制的僵化:“面对法式古典主义的优雅和‘三一’铁律,直要等一百年,莎翁的夸张才能才获得承认,成为戏剧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位“吉儿”的存在在法国才可正常化。”当然这文章或许是雨果为了力挺其长子弗朗索瓦·雨果的新译本而写(1864年弗朗索瓦·雨果译出新版《莎士比亚全集》),称他儿子的译本才是“未加嘴套的莎士比亚”。今天看来,小雨果的这套译本的翻译策略虽比较自由,但其忠实性和可读性远远高出了以往的任何版本。雨果曾对这浩如海洋般的作品发出感叹:“这种有效的刺激,这种净化宇宙的苦涩,这种缺了它一切都会腐烂的粗燥的盐,这些愤怒和平复,这永恒之意外,这无尽变化着的单调中辽阔的奇迹,这动荡过后的水平面,这永远躁动不安的广大地狱和天堂,这无休无止,这深不可测……埃斯库罗斯,以赛亚,尤维纳利斯,但丁,米开朗琪罗,莎士比亚,注视着这些灵魂,犹如凝望面前的浩瀚海洋,完全是同一种感受。”
雨果的身上聚集了自由的浪漫主义所有的理念,同司汤达一样,他追求真实感、悦众感。在1827年的《克伦威尔序言》中,他写道:“赞歌为永恒而写,史诗彰表历史,戏剧描述生活。赞歌的特征是天真,史诗应该简洁,戏剧的特征理应是真实。赞歌的主角是巨像,史诗的主角是巨人,戏剧的主角是人。赞歌靠理想为生,史诗靠伟大而生,戏剧靠现实。总之,这三种诗来自三大源头:《圣经》、荷马与莎士比亚。”寥寥数语写足了莎士比亚在雨果心中的地位。在“赫那尼”这场著名的古典与现代之争中,莎士比亚成了所有浪漫派主张的典范。他是夏多布里昂眼中整个英国文学的代表,是大仲马的偶像,是维尼、缪塞的灵感源泉,是司汤达的榜样。
雨果之后,法国批评界与演出界是否就真的完完全全接受了“吉儿”式的莎士比亚?不,还没有那么彻底。1859年,唯美派的代表戈蒂埃指出,法兰西喜剧院是除法兰西学院之外的另一个固守“风雅”的堡垒,那里只肯排演莎士比亚的一些迷你短剧,且更愿意采用像杜西斯那种守旧的改编版《奥赛罗》,而非诗人阿尔弗雷德·德·维尼的直译本。司汤达在《拉辛与莎士比亚》一文中指出:“幻想是衡量一部剧作好坏的必要条件;幻想是为了让观众感动,感动是戏剧的核心理念,感动必来自于真实的生活。在这一理念面前,‘三一律’是无力的。”
浪漫主义给法国戏剧带来了以往被忽略的主题:社会理想,作为灵魂镜子的自然,新形式中找到的创意,想象力,梦幻虚构,“自我的宣泄”,对过程的、异域的、神秘之境的向往。戏剧性有了新的追求,死亡主题、暴力主题愈发地吸引观众。在司汤达看来,莎士比亚因其自由、现实、生动而光芒四射。比如司汤达1823年出版的《拉辛与莎士比亚》,就是发生在“一个古典主义者”和“一个浪漫主义者”之间的文学的虚构交流,就是两种写作方式的对立,比较路易十四时期独裁高压下的拉辛,和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宽松而理想化的语境中摆脱了束缚的莎士比亚。在司汤达看来,拉辛呈现出最法式的戏剧特征:纯粹、极简、崇高,拒绝丰富,严格‘三一律’。对于拉辛而言,一切都已提前安排好,每个时刻都节奏紧凑。莎士比亚是最英式的戏剧特征:超出戏剧本身,走向文学、文字、思维方式,热情洋溢、纵情奔放、丰富繁盛,形象复又创造形象,总有些意外插曲。关于暴力、悲剧,拉辛是深沉的、感人的、身不由己的;莎士比亚的观众是意识到的,清楚整个犯罪的过程,悲剧中有喜剧,喜剧也得按照悲剧来编排。
莎士比亚丰富的词汇、象征的价值、刻画内心的复杂视角、揭露真实世界的旨意、哀恸悲怆和阴郁可怕的基调,已渐渐地为那个时代所接受。“雨果文艺小组”除了上述人等外,还有巴尔扎克、圣伯夫、梅里美、德拉克罗瓦、柏辽兹……一切艺术的交流都本着同一个思想: 去腐除旧,自由创新和想象。1828年维尼同德尚合作译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却未能上演。1829年他又同布吕杰合作译出了诗体版的《奥赛罗》,删除了人物比恩卡的角色,更改了结局,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却反响平平。
自1827年起,莎士比亚的作品在法兰西的舞台上越来越多地被演绎,并相继大获成功,浪漫派们悉数出席观看每一场演出。比如德拉克罗瓦从中汲取灵感,创作了《哈姆雷特》的系列版画。舞台上演员们强烈的情感表达,被他体现在色彩的运用上,然而脸部线条却始终是模糊的。1838年德拉克罗瓦又创作了版画与速写系列《奥菲丽亚之死》,与安格尔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大唱反调。莎士比亚戏剧也深深地感染了柏辽兹,他相继写下了多部幻想交响曲,题材取自《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菲丽亚之死》和《哈姆雷特的葬礼》。这些又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天才少年兰波,写下了著名的长诗《奥菲丽亚》。可见,莎士比亚在法国的广泛接受和改编,绝不仅仅局限在戏剧领域。这种现象的传递,标志着莎剧重获认可,自此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冲突平息,对法国文坛实在影响巨大。所以说直到十九世纪末,莎士比亚才被法国公众真正接纳为“伟大的戏剧作家”。
二十世纪上半叶,莎剧登堂入室,真正赢得了法国的观众和演出的空间,并四处开花,成为各大剧院的常年固定剧目。如1947年在阿维尼翁,由法国伟大的话剧演员让·维拉(Jean Vilar,亦是“阿维尼翁戏剧节”的创始人)出演《理查二世》,轰动一时。1948年《哈姆雷特》在巴黎上演之际,法兰西喜剧院院长巴罗(Jean-Louis Barrault)宣布说“莎士比亚在法国上演的场次首次超过了拉辛:对法国人而言,莎士比亚成为了一种需要”。不可否认,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法国观众,或许会认为暴力粗犷的真实感远比风雅品位更接地气。
2015年12月5日至2016年5月30日,《罗密欧与朱丽叶》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此剧距上一次在巴黎演出已相隔半个多世纪。“阿维尼翁戏剧节”的总策划奥利维埃·毕在接受法国文化电台的采访时说:“莫里哀写过不少烂剧,彻底不能演。莎士比亚没有烂剧,只有被人遗忘的剧,其最不见经传的作品,也都是不可思议的杰作,比如说那部《辛白林》。莎士比亚的现代意义,远超荷马。”莎士比亚的戏剧语言是丰富的、多义的,折射着当代之光。法国比较文学学科泰斗布吕奈尔教授说:莎士比亚留给法国文学的财富,远未达到能做最终结论的时候,文学性的研究比较容易流于表面,我们更需要从历史的、文化接受的维度,各自寻找英法文学的内在魅力……”
原载于外国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