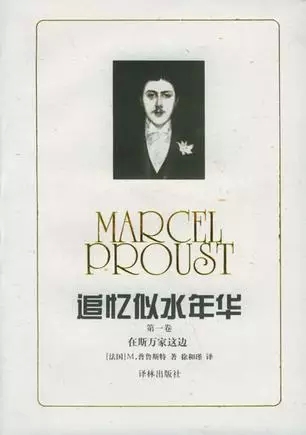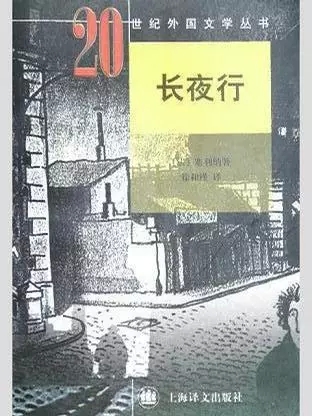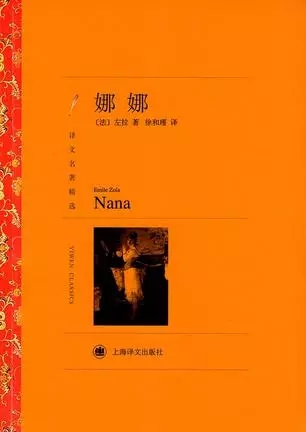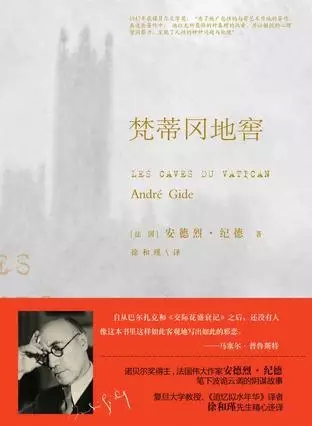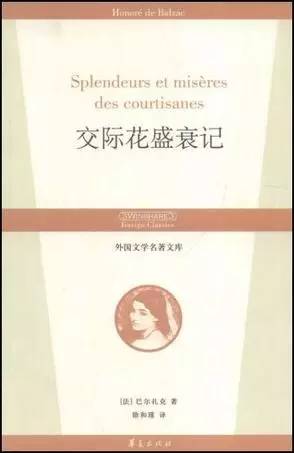2015年8月15日下午14时01分,中国资深翻译家、复旦大学法文教授徐和瑾因患肠道癌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病逝,享年75岁。
徐和瑾1940年生于上海,一生从事法语文体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和法国文学作品翻译。曾经担任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理事,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法国
普鲁斯特研究中心通讯
研究员、法国普鲁斯特之友和贡布雷之友协会会员,曾被聘为巴黎第七大学和拉罗谢尔大学客座教授。
徐和瑾是“文革”后最早向中国读者介绍普鲁斯特的学者之一。1958年至1962年就读于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学习。1962年至1964年在复旦大学外文系任俄语教师。1964年至1966年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德法语系进修法语。1970年至2000年在复旦大学外文系任法语教师,在职期间曾任法语教研室主任、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理事。1978年至1979年,徐和瑾去法国进修一年,由此确定了自己在语言研究和文体学方面的学术方向。1985年,徐和瑾与他人合译了第一本译作巴尔扎克的《交际花盛衰记》,此后他陆续翻译了米歇尔·代翁的《一辆淡紫色出租车》、让·皮埃尔·韦尔代的《星空:诸神的花园》和《思考宇宙》、芒迪亚格的《黑色摩托》、塞利纳的《长夜行》、安德烈·莫洛亚的《普鲁斯特传》、拉巴雷尔的《杜拉斯传》、纪德的《伪币制造者》和《梵蒂冈地窖》、莫泊桑的《漂亮朋友》、左拉的《娜娜》、杜拉斯的《英国情妇》和加缪的《局外人·鼠疫》、莫迪亚诺的《地平线》、莫洛亚的《追寻普鲁斯特》等。2004年起,他以一己之力翻译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代表作《追忆似水年华》,目前已经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四卷。另独自编写《新法汉小词典》,编写《大辞海·外国文学卷》中法国文学的全部条目等。2010年获得中国翻译协会颁发“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
翻译家总把自己淹没在文本里面,让读者自然淡忘他们的存在,徐和瑾老师亦是这种境界。
在这里,谨向徐和瑾老师致以哀悼,感谢您为我们带来了那么多法国文学经典,希望老先生一路走好。
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云也退作为书评人、撰稿人,曾于2012年对徐和瑾老师作过专访,之后刊于《生活月刊》。在经作者同意后,将本文与大家分享,以纪念徐老师。
徐和瑾访谈:年华是用来磨的
“我本来可以做个理科生的。”
徐和瑾打开电脑,给我们看他新扫描的一张老照片:地上搁着一架飞机,一翅着地另一翅翘起,飞机前坐着个两臂抱膝的少年,脸上挂着那个年代的人下意识的沧桑感。“这就是我。”徐和瑾说,“这架滑翔机是当时外国语学院(当时还不叫大学)组织造的,我还是主力。”
照片足以让人对五十年前的高校心生好奇。徐和瑾讲,当时跟他报名参加这个任务还有两个女同学,不过,“我还真是搞过飞机模型的,她们都没搞过。”照片里的背景是一片矮矮的、如同工棚一样的校舍,早就消失了,前景中的滑翔机搁在旷野似的操场上,看上去足有四米来长:“飞是飞不了的,要是飞起来还了得了。”——要是真能飞起来,徐和瑾恐怕也不会留在上外了。
徐和瑾和周克希两位退休的上海翻译家各自在独力翻译《追忆似水年华》。周与徐年齿相仿,他每次出席文化活动,或多或少都会提及自己当年由数学转行的轶事,相比之下,知道徐和瑾的理科生素养的人就少得多了。除了做飞机,另一个能说明徐和瑾与理科的亲近的证据是他给北京《科技画报》投过稿。六十年代初,《科技画报》的稿件资源和翻译人手都短缺,发出英雄帖对外征译稿,并特别指出,最欢迎来自罗马尼亚语或匈牙利语报刊、书籍上的科技译文。在外国语学院,徐和瑾主修俄语,后来又学了一些匈牙利语和捷克语,就想借此试手,他找了匈牙利《人民自由报》上的一篇讲太阳系的匈牙利语文章,译好了投寄过去。
“杂志那边没给音讯,我估计他们不信,觉得我大概是抄抄现成的。过了一阵子,我又在一本很小的匈牙利语杂志里找了一篇讲两千年前的药方的文章,翻译好了寄过去,他们这才信了。”之后,《科技画报》连续十几期都发了徐译的科技文章。
听徐和瑾忆旧,感觉他海外关系真不少。比如,六十年代的时候他就与东欧朋友有了飞鸿往来;再细打听,这些往来的机会原来都是他自己仔细搜集来的,而且同他爱好众多、交游广泛有关。
“我有国内朋友在东欧,知道我喜欢集邮,回来时捎给我一些东欧出版的集邮杂志。我在那上面看到有个栏目是发布海外读者的征友信的,想试试看,就给杂志去了封信,自我介绍说是一个中国学生。杂志果然登了我的联系方式,之后我一下子收到了好多匈牙利人写来的邮件,我在这些信息里挑了几个跟他们联系,其中一个年纪四十多岁的,后来跟我的通信特别多。”
对于邮友来说,只要是海外来函,哪怕收到一个空信封都是有价值的。徐和瑾不但写信,还把自己的匈牙利语译文也寄给那个朋友看,对方寄来的信他也都收藏着,一直藏到今天,明信片和书信都还完好无损。就保存资料而言,徐和瑾无疑是个行家。
不过,最初学的俄语和后来学的捷克语、匈牙利语都没能成为徐和瑾日后的主业。他毕业后进了复旦大学当老师,由于复旦需要法语老师,而俄语人才过剩,就把徐和瑾又派回上外去进修两年法语。在这两年期间,四清运动开始了,徐和瑾第一年曾想听高年级的班,运动一来只好作罢,老老实实从一年级学起,到第二年学生回来,才又跑去了四年级的班。既然转入了法语,徐和瑾也就一五一十地开始搞他的研究。在学术上,他的研究方向是文体学,这就与普鲁斯特挂上了关系。
“我是国内最早介绍普鲁斯特的人之一,”他淡淡地说,看不出引以为豪的样子,“我是学者,感兴趣的是文体。”
他首先是学者,其次才是翻译家——所有熟悉徐和瑾的人都会这样说。普鲁斯特的意识流文字,那种连贯不断、犹如一个套一个、一个接着一个打开的文件夹的描述性语句,徐和瑾最初是以论文的方式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八十年代初,他写的《马塞尔·普鲁斯特》一文发表在《外国文学报导》上,被视为有开创性的一篇文献,在其中,他以当时所能掌握的理论资源作了基本的文体分析:句子如何结构,意义表达如何既主观又精致有序,并非纯粹的胡思乱想。读他的文章,你看不出他有多么突出的文采,反而严谨,搜集的资料全面,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些才是他至今不变的标志。
毋庸讳言,作为学者的徐和瑾并不以文学翻译见长,可他偏偏还翻译了一些五星级难度的文学作品,例如另一位法国作家塞利纳的《长夜行》,此书中所用的连绵不断的市井俚语,足以让每个译者望而生畏。当韩沪麟组织《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时,徐和瑾起初想选第四卷译,后来安排到手中的却是最后一卷的上半部分,主人公在此卷里有大量的议论、分析,他要对自己怎样开始写作做一个回顾总结,捎带着要评价自己所处的时代。日后,徐和瑾很坦率地承认,翻译《追忆》第七卷时的译笔有生涩的地方。在第七卷中,类似这样有些拗口的句子并不少见:
“‘另外,我是否要向您承认,’絮比安接着说,‘我对于得到这类收入并没有很大的顾忌?人们在这儿干的事,我不能再对您隐瞒我是喜欢的,是我生活中的爱好。’”
徐和瑾不讳言自己的缺点,有时甚至过于诚实。为了说明自己是如何一点一滴进步的,他下意识地用一种小学生习作的口吻来讲述一些重要时刻:我参加了什么,我学到了什么,我的收获很大。1997年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中法翻译讨论会就被他视为这样一个时刻。“翻译多了之后,特别是1997年在复旦举办中法翻译讨论会,(我)跟翻译界的同行有了更多的接触,逐渐感到在正确理解原文的同时,也应该注意中译文的流畅,因为译作毕竟是给中国人看的。”
在这次讨论会上,徐和瑾和法语翻译界的几位才子,如施康强、罗新璋都见了面,与多产的翻译家李玉民更是一见如故,李玉民所译《巴黎圣母院》、《人间食粮》等法语名著都以文采飞扬、诗意斐然著称,徐和瑾深感佩服。“我们就此成了好朋友,他经常打电话来问候我,现在天冷了,他跑到广西那边住着——他在那儿有房子用来度假。”说这话的徐和瑾,还坐在复旦七区自己老旧的小屋里:老旧的护墙板,老旧的玻璃板桌子,老旧的淡黄色木门。新的东西也有:新买的扫描仪,46寸的液晶电视屏,还有一套通过网络订购的最新版007电影碟片。
当新世纪初,译林社的韩沪麟重新找到徐和瑾,邀他完整地重译一遍《追忆》时,徐和瑾已经身背法国“普鲁斯特之友协会”会员这一身份,也已被聘为巴黎第三大学普鲁斯特研究中心通信研究员,普鲁斯特研究但凡出了一点新动态,他都能及时掌握到。他说,出版社不是随便找上他的:“他们专门把我拉到南京去开会研究这件事。”
最后应允下来,还是出于一个字:爱。
爱普鲁斯特,对这些文革前接受高等教育的老一辈来说尤其不容易。比如1939年出生的韩沪麟,虽然几乎以一己之力主持了七卷本翻译这项宏大的工程,但他坦言普鲁斯特的文字对自己并无太大的吸引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维框架、情趣和文化风尚。韩沪麟最喜欢的法国文学,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如都德的《磨坊信札》,都是传统的写实主义小说或乡村小品。《追忆》于他则更像是一个事业的坐标,是为了证明自己在远离文学与文字理想这么多年后,依然可以“做出一点什么”。
徐和瑾也是同样,以他质朴、谨慎的性格,表面上看,汪洋自肆的普鲁斯特与他并不般配,距离巴尔扎克—傅雷或纪德—盛澄华那样的“天生一对”更是遥远。但是,徐和瑾理科生式经年累月的孜孜矻矻,积累材料,磨砺译笔,硬是让自己走过的这条路看起来是一种必然。他手头有《追忆似水年华》历次修订的各个版本。2002年,在应邀去译林社谈重译合作时,他谈的一件事就是确定重译所依据的版本:显然,他首先是一位“专家”,而不是像很多文艺青年想象的那样,是个浑身上下散发着小资情调的风雅老先生。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法国学界开始根据普鲁斯特的手稿来校勘这本书,后来陆续出了好几个版本。2008年,他们开始整理普鲁斯特的练习簿手稿,每本整理两册,一册是手稿影印本,另一册整理成印刷文字。”谈起《追忆》的版本掌故,徐和瑾可谓是信手拈来。八十年代翻译第七卷时,他用的是从图书馆里借来的一个袖珍本,而现在,他已经有了包括米伊主编的弗拉马里翁版、七星文库版等多个版本。译好这样一套书,版本的全面是特别重要的。这些成套的外版新书就堆在徐和瑾的书房里,对面是靠墙的三个年迈的书橱,里面几乎每一本书都已被岁月磨成尘灰色,书橱玻璃门也快不行了,移动起来滞涩无比。
2004年,徐译《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终于脱稿,在翻译过程中,他问了法国老友米伊六百多个问题。不管什么时候去读,普鲁斯特都是那么难。“不过现在,我觉得他还是可以翻译的。”徐和瑾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我毕竟是过了十几二十年后着手重译,现在我有了更多的资源,文字跟当年肯定也不一样了。”网络上读者们摘抄了许多徐译第一卷里的美句,我们从中可见,勤恳的徐先生已非吴下阿蒙;他自己也说,对句子节奏感的把握比当年强了很多,一时译不好也不要紧:“慢慢磨呗。”
信奉“磨”功的徐先生太沉得住气,大半生都不显山不露水,重译《追忆》九年多来,他不声不响坐啃书山,“社会活跃度”很低。当年在复旦评教授,申请的人都要考第二外语,对他来说也就是考个英语写作。“我一个小时就交卷了,另一个同事交了白卷。可结果还是他先评上,因为上边要提拔他当副系主任,就这么简单。”徐和瑾两手一摊,“这样的事情很多,但也没什么,我无非就是晚评上一两年嘛。”
近几年来,法国政府部门嘉奖于中法文化交流有功的中国籍翻译家、教育家的新闻屡见不鲜。徐和瑾曾有机会,也是因为各种原因与奖项失之交臂,现在退休了,少了学校的推荐,获勋更是微乎其微。对这些,他嘴里没有半点抱怨,甚至《追忆》已经获得的反响都没能打乱他不紧不慢的节奏。当被问起最看重哪一项个人成就的时候,他的回答让人有些意外。
“《新法汉小词典》算一个吧。这本词典是我2002年签约,在翻译《追忆》的间隙编完的,读者都说很好用。后来我把书寄给了法国著名的汉学家、诗人程抱一。前两年程抱一携女来厦门开讨论会,席间对(复旦的法语老师)袁莉说:这本词典是他看到的最好的法汉词典。”听到袁的传话后,徐先生很欣慰。
“这很重要——我毕竟是个学者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