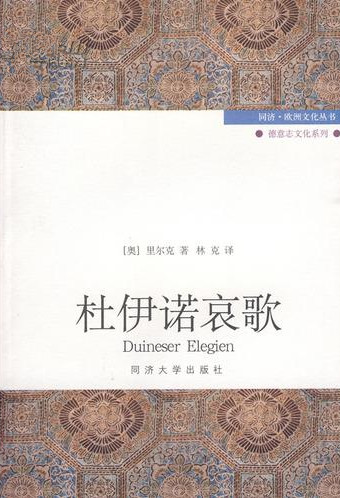里尔克的翻译介绍,在民国时期就形成了一定的气候。冯至、陈敬容、梁宗岱、卞之琳等都翻译过他的诗。经过一个历史时期的沉寂,到八十年代,里尔克突然被年轻人重新追捧起来,无论读没读懂他的诗,他们嘴里都会时常提到里尔克这个名字。
作为诗人的里尔克,在中国大概已经成了一个偶像。既然是偶像,他就会被标签化、平面化,形成一个符号,从而隐没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思想或风格,这就造成了对这个偶像的理解和分析的障碍。既然是偶像,人们就不再敢于质疑与他相关的问题,也消减了对他深入了解的欲望和勇气。我跟大多数人一样,当时对冯至所译的《严重的时刻》也表示欣赏,可其实,我一直以为这个“严重”是“发生了什么严重事情”的“严重”,直到很久以后才弄明白,它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严肃”,不过是民国时的用语。说真的,当时我对里尔克真的兴趣不大。
近年来,国内引进的外版图书渐渐多起来,于是读到了德英对照、法英对照的里尔克。对照德文、法文一读,竟使我大开眼界。在里尔克的德文诗里,我第一次发现,里尔克的《致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五十五首十四行诗,每一行都是押韵的!这需要花费他多少时间去想那些韵脚啊!《图象集》里的短诗,语句都安排得极为精巧。而他的法语诗,都是音节数相当整齐的诗句(要知道他是用外语在写作!),似乎每一个音节都可以滴出新鲜的果汁来!
我的德语和法语水平都很有限,所以谈里尔克,于我是很不恰当的,我向来没有在人跟前说过我读懂了里尔克。但是对于译成中文的里尔克,我似乎还能站在门外谈几句。
跟许多爱好诗歌的朋友一样,我阅读像里尔克这样艰深的诗人,往往会搜集各种译本。但是里尔克诗的不同译本之间,在意思上(更不用说意境上)往往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或许手头的译本越多,越是搞不明白其真相如何,让读者非常为难。如《杜伊诺哀歌》第八首的第一节:
动物以睁大的眼睛,凝望着
开放的世界。只有我们的眼睛
反逆似的,有如罗网,在它四周围置着,
环绕着其自由的出口。
我们只有从动物的面容去认识
外界是什么;因为即使幼小的孩童
我们令他转向且协迫着向后凝望
(“协”似为“胁”之误)
造型的世界,而不是在动物的眼光中
如此深邃的、开放的世界。免于死亡的威胁。
只有我们凝视着死亡:而自由的动物
始终把其没落置于身后,
神在前引导,当行进时,就走向
永恒,如喷泉一般。(译本一)
造物的目光专注于敞开者。
唯有我们的目光似乎已颠倒,
像设置的陷阱包围着它们,
紧紧包围着它们自由的起点。
那外间实在的,我们有所获悉,
单凭动物的面目;因为我们
早已让幼童转身,迫使他向后
观看形象,而非敞开者,它深深
印在动物的脸上。超脱于死亡。
唯有我们看见死;自由的动物
始终将自己的衰亡留在身后,
前方有上帝,它若行走,则走进
永恒,一如泉水奔流不息。(译本二)
生物睁大眼睛注视着
空旷。只有我们的眼睛
仿佛倒过来,将它团团围住
有如陷阱,围住它自由的出口。
外面所有的一切,我们只有从动物的
脸上才知道;因为我们把幼儿
翻来转去,迫使它向后凝视
形体,而不是在动物眼中显得
如此深邃的空旷。免于死亡。
只有我们看得见它;自由的动物
身后总是死亡而
身前则是上帝,当它行走时它走
进了永恒,有如奔流的泉水。(译本三)
动物张足眼睛看,视线遇物穿透如
无物。我们的目光恰恰
相反,呈井状围住观察对象,
留出自由出入的井口。
外部世界是什么,我们单看动物的
脸相便知:因为我们把婴儿倒竖
起来强迫他倒着看
并没有动物脸上
深刻的空茫感:死一般无羁。
只有我们发现了死;自由自在的动物,
身后永是沉沦
身前是神,而走
是在永恒中走,恰似泉水流淌。(译本四)
用所有的眼睛造物看的都是
那空旷。只有我们的眼睛是
仿佛反过来的,环绕着它们设置着
如同陷阱,围绕它的通畅的出口。
外部有什么,我们只能从动物的脸上
知道;因为那幼小的孩子
我们已经把他转向,强迫他倒过来
看形态,而不是那空旷,那种
在动物的脸上如此深刻的。自由于死亡之外。
它只有我们才看得见;对那自由的动物,
衰败永远是在它身后的
而它面前是神,它走动时就走
进了永恒,就像泉的流动一样。(译本五)
自然界把所有的目光投向外面的
旷野。只有我们的目光往后望
并且在植物、动物和婴孩
进入自由的时候像一个圈套围住它们。
我们只能从这动物的目光里
看到那里到底有什么;因为我们
强令婴孩到处逛,好让他看到
物体——而不是深藏在动物
面孔里的旷野。摆脱死亡。
只有我们能看到死亡;自由的动物
永远衰落在后,上帝在前,而当它行走,它已在
永恒中行走,一如喷泉。(译本六)
不懂外语而读外国翻译诗,有时就像是在猜谜一般。首先是这段文字的第一个主语,从上述译本中看,既有“造物”、“自然界”,又有“动物”、“生物”,让人莫衷一是。所幸的是,从后一句我们隐约知道,它多少是与我们人类相对的一种东西,而且是有眼睛的,那么就不妨说是动物界(Kreatur)吧,以区别于下文中的动物(Tier)。接着是那个“反逆”、“颠倒”、“相反”、“往后望”的眼睛,让人颇费心思来猜想,因为把眼睛(也可以理解为眼珠子)“反逆”或“颠倒”过来,实在与观看无关,所以这里的眼睛指目光也许更加恰当一些。于是反推回去,前面所说的“用所有的眼睛”,一定不是说有“多少”眼睛在看,而是说竭尽全力(目力)去观看。
然后是那个被“包围”、“围住”或“环绕”的那个东西,译文中既有复数(它)又有单数(它们),不知道这里是回指“动物”、“动物的眼睛”,还是回指其它什么(如果读者不同意第一个主语是指“动物”,那还可能回指“造物”、“自然界”)。译文中出现这样混乱的指涉,还谈什么欣赏诗中的韵味?
现在再说那个小孩,我们究竟让他怎么了?是让他“转向”、“转身”、“翻来覆去”、“倒竖”、还是“到处逛”?我们究竟让他“向后望”、“倒着看”、还是“倒过来看”?要知道,这些动作之间有多大的区别!后面是一个短语:Frei von Tod(自由+远离+死亡)。从译文看,“免于死亡的威胁”、“超脱于死亡”、“摆脱死亡”、“死一般无羁”、“自由于死亡之外”,前三种译文与后两种译文,以及后两种译文之间,有鸿沟一般的区别。
说到动物,后面一句的译文是,“始终把其没落置于身后”、“始终将自己的衰亡留在身后”、“身后总是死亡”、“身后永是沉沦”、“衰败永远是在它身后的”、“永远衰落在后”,这样的译文,让人很难理解。其实它的意思是说:自由的(frei)动物永远把死亡抛在后面(像在赛跑一样),迎着前面的神,向前行进。把死亡抛在后面,就是远离死亡(Frei von Tod),就是走向永恒,这里说的是动物面对“开放的世界”的自由状态。动物跑在前面,因此看不见死亡,所以前文说:只有我们才能看见死亡。诗人在这个短语的下一行重复使用frei(自由)这个词,正是想把这两行的意思联系起来。这种文字上的关联,译文中似乎没能考虑到,或者虽有考虑,但表现得并不理想。
这里只是列举了《杜伊诺哀歌》中的一小段文字而已。诗歌翻译,字对字的翻译未必就是最忠实的。译语的选择,要顾及全篇的理路和脉络。同时还要注意“文字修辞”与“文学修辞”的区别:文学修辞是诗人创造性的一部分,在翻译中尽可能不要丢失;而文字修辞往往与某种语言本身密不可分,在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需要找到一种替代的表述方法,有时只能放弃。比如前述“用所有的眼睛”是一个习惯用语,只是文字修辞而已,并不是文学修辞,不必依样画葫芦地译出来。
现代诗的创作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意象的转换,但如何在翻译中将意象安排得恰到好处,恐怕是译者必须通过考察两种语言的习惯,仔细掂量的一个重要方面。过于密集的意象和繁复的转化,可能会使读者在不知道哪个环节上发生错乱,从而误解原诗的意思。诗歌翻译是一项精细的活动,对这些表述的细微差别尤其要细心体味。
如果说里尔克是一个注重诗歌技巧,对语言千锤百炼的诗人,他的作品竟有差别如此之大的译文,我虽然是德文诗的门外汉,也不禁要怀疑其中某些译文,或者某些译文的某些部分是否过于粗糙。读着这些译文,我有点替那些不读原文、把里尔克诗的译本奉为圭臬、开始学写现代汉语诗的年轻朋友们担心。
在外国诗的翻译园地里,如此大面积地种植这些粗粮,会使得读者的口味变得很重,难以分辨米酒和高粱酒的区别,花菜和西兰花的不同,红烧肉和东坡肉的差异。正如不习惯吃辣的人,在吃正宗的重庆火锅时,放在锅里的究竟是什么菜可能不很重要,关键是那股子辣劲儿。虽然对于喜欢吃辣的人来说,重庆的辣、成都的辣、长沙的辣、南昌的辣,以及其它地方的辣各有特点,但是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菜都在“辣”字上做文章。比如江浙一带的菜肴可能偏于清淡,而这清淡里面的花头,也不比各地方的“辣”法更少一些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诗的引进和翻译可谓相当繁荣。但哪些外国诗人可以先引进,哪些外国诗人要推后一些引进,恐怕是要仰赖译者和出版人仔细考虑的。有些外国诗人在汉语语境中还没有铺好“跑道”,不适合“飞机”降落,强行降落的话,必然造成“机毁人亡”:译者自己还没理解就动手翻译,或者译者虽然理解了,但在汉语中找不到恰当的表达方式,勉强表达了,读者阅读时苦不堪言。里尔克可能是属于需要稍微推后一些引进的种类。
里尔克的诗很醇,味道很正。说它正,是因为它有丰富的欧洲传统。他前期的诗,包括《图象集》和《新诗集》中的大部分诗,都是格律诗。尤其是他的法语诗,在押韵上,里尔克做到了几近于苛刻的完美,在这一点上,他可以直追波德莱尔和魏尔伦。里尔克用词精准,绝不拖沓,在这一点上,他可以直追福楼拜。里尔克在思想上是优秀的,在语言上也是超绝的。里尔克的诗,特别是《杜伊诺哀歌》,在英语国家,虽然据说翻译得也不够完美,但据我阅读、比较过的七、八个英译本来看,还不至于如此让读者为难。
在里尔克的诗歌艺术里,语言技巧占了一个显眼的位置,而且是相当过人的。如今谈论外国诗歌的,很少谈及写诗的语言技巧,遑论音韵与格律。“技巧”这东西,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遭到不少年青诗人的鄙视。我们的现代汉语诗创作有不少都采用“自由体”形式,诗歌评论一般也主要谈论诗中的思想;这几乎已经渗透到我们的创作和批评的潜意识。即使在谈论诗歌这种对语言要求极高的文学体裁时,形式问题依然处于次要的地位。我想套用艾略特评论庞德的一句话,如果里尔克没有经历过前期诗歌格律严谨的创作过程,很难想象他后期会写出如此宏大而深刻的“自由体”组诗《杜伊诺哀歌》。
里尔克诗的翻译,除散见于各种诗集的篇什之外,单独成册的选译本现在已有十多种,但据说只有零星的一两种(而且只选译个别篇目)是由精通德语的翻译家,完全从德语原文翻译过来的。我真希望这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