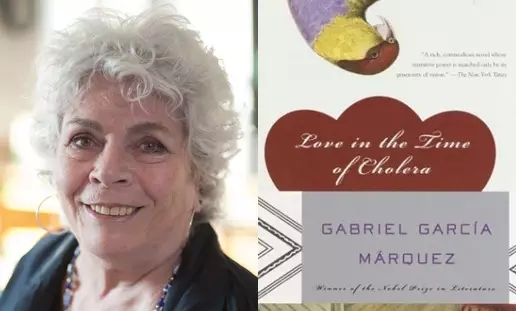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霍乱时期的爱情》英译本
除了经济回报问题之外,翻译对创造性的艺术家的影响还体现在另一种方式上,虽然不那么明显但更重要,产生的后果也更加不寻常。正如沃尔特•本雅明在上文引用的篇章里指出的,文学翻译为一种语言输入了影响、替代性选择和结合的机会,如果在单一语言的领土之外没有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风格和观念的存在,没有大量文学的存在,这些都是根本不可能的。换句话说,翻译文学对被讨厌地称为“目标语”也就是译入语会产生重新确认的和扩张性的影响。
1964年,罗伯特•勃莱(Robert Bly)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聂鲁达(Neruda)的惊讶”,其中他直接谈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倾向于把现代想象力与怪异想象力联系在一起,它开始于从一个话题转向另一个话题的前进、停止、转向。在聂鲁达的诗歌里,想象力在向前推进,加入到想象力不断高涨的整个诗歌的浪潮里。他是抓住表面现象下的流动趋势的新潮人物。
在下面移动,他知道底层的一切(这是了解事物本质的正确方法)因此从来不会困惑于找不到名字。与他不同,美国诗人就像在树林里从一棵树摸到另一棵树,从一个房子摸到另一个房子摸索前进的盲人,每件物品都触摸很长时间,然后,当我们已经知道它是“房子”后才说它是“房子”。
翻译所能产生的艺术发现的影响对任何语言和文学的健康和活力都非常重要。这或许是国别文学的历史常常排除某些作家间特别重要联系的原因之一。建立在国内和国外明确区分基础上的“国别文学”是个狭隘的、限制性的概念,在某些地方,这种区分当然是有道理的和有用的,但在写作中,翻译将这种差别消除了,它否认或拒绝因为建造巴别塔而受到上帝的惩罚,或至少要消除其最糟糕的分裂性影响。
翻译确认了众多语言组成的世界连贯的和统一的文学经验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翻译称赞语言间的差别以及语言表达的人类经验和感受的多样性。我认为这并不矛盾。相反,它证明了文学和翻译的整体性和包容性。
翻译带来的语言间富有成效的交流的一个例子是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和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之间持续的联系。马尔克斯年轻时就对福克纳的小说有难以满足的渴望,贪婪地阅读了他小说的西班牙译本,同时还有其他语言的其他作家的译本。多年来他常常谈到福克纳是他最喜欢的英语作家,这成为哥伦比亚总统和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1995年夏天位于马赛的葡萄园(Martha’s Vineyard)的威廉•史泰朗(William Styron)家中晚餐上长时间谈话的主题。(克林顿说《百年孤独》是过去50年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是他最喜欢的小说)。当时在场的还有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当他说他最喜欢的书是《押沙龙、押沙龙》时,克林顿站起来背诵了《百年孤独》中班吉(Benjy)独白的片段。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为小说而生》中对《八月之光》(福克纳的小说)的阅读就像主调,叙述他与母亲一起卖掉阿拉卡塔(Aracataca)的老房子的旅行。“通过借来的书和译本,我已经阅读过小说家技巧学习所需要的所有书……福克纳是我的最忠实的守护神”。接着他说“我呆在房间里读我碰巧或者幸运地得到的书。这些书就像刚刚烤熟的面包,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因为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的印刷厂刚刚印刷出来。让我感到幸运的是,我以这种方式发现早就大名鼎鼎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劳伦斯(D. H. Lawrence)、赫胥黎(Aldous Huxley)、格雷厄姆斯•格林(Graham Greene)和吉尔伯特•切斯特顿(Gilbert Chesterton)、威廉•埃里希(William Irish)、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等很多作家。”
关于詹姆斯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他写道:“它不仅是我从来没有怀疑在自己身上也有的真正的世界性发现,而且也提供了宝贵的技术帮助我解放语言,帮助我在自己的书中处理时间和结构问题。”最后,这是他描述第一次阅读卡夫卡的影响,“我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平静地入睡,这本书就是斯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的《变形记》,这是由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罗萨达(Losada)出版的博尔赫斯的虚假译本,本书的第一行就决定了我的生活的新方向。今天它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伟大技巧之一。”他或许称该译本是“虚假的”,因为正如他描述的从博尔赫斯那里学到的东西那样,作者需要做的只是写被认为真实的东西。
无论如何,在这段短文里,这个著名小说家令人印象深刻地求助于年轻作家在小说写作的技巧上所受到的广泛而清晰的教育。这个成就如果没有文学翻译的存在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些书和他阅读过的其他书对他走上作家道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使他能作为学徒阅读远方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事实上成为他的导师。
有人曾说福克纳是用英语写作的最著名的拉美作家,这种描述或许不仅仅是俏皮话。他似乎继承了给他带来深刻和广泛影响的塞万提斯风格,然后把它转变成英文,这给后来的西班牙语作家产生既积极又消极的双重影响。
而且,塞万提斯创造了现代小说的形式和形态,无论小说作家的语言是什么,这种体裁转型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欧洲小说的发展,尤其是18世纪的英国和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的开创性作品直接来自《堂吉诃德》的模式,该书几乎是刚一出版就被翻译成英文。托马斯•谢尔顿(Thomas Shelton)的英文版出版于1611年,这是塞万提斯1605年出版的小说的第一部分第一次被翻译成外文。
据说莎士比亚曾打算根据《堂吉诃德》第一部分交叉叙述之一的主人公卡德尼奥(Cardenio)的冒险写一个剧本,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实际上写了这样一个剧本但不幸丢失了,这些猜测在我们看来特别令人好奇,因为英国有谢尔顿译本的存在和成功,这些译本开创了塞万提斯影响小说成长,影响小说家的写作方式,当然也影响福克纳的写作方式的漫长和多面的历史。
毫无疑问,在20世纪中期,福克纳是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当代英语作家。他的令人想起塞万提斯回声的雄辩和响亮的巴洛克风格对西班牙语读者来说是熟悉的,但我相信他对拉丁美洲小说发展的深刻重要性的决定性因素首先是被称为“爆炸时期”(the Boom)的文学现象是福克纳对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是人的神秘的、大历史的、多年代的视野。不仅加西亚•马尔克斯而且卡洛斯•富恩特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以及其他当代拉美小说家都得益于福克纳(当然也有塞万提斯)很多。如果塞万提斯、福克纳和其他这么多作家没有被翻译出来的话,这种丰富的文学杂交没有一项是可能的。
同样的,如果不考虑到加西亚•马尔克斯(更不要提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和胡利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讨论英语世界的当代小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福克纳在拉美的影响发生在说西班牙语的大部分地区一样,从译本中体现的马尔克斯作品的影响明显地体现在著名作家如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唐•德里罗(Don DeLillo)、迈克尔•夏班(Michael Chabon)等人身上。
思考这些事非常有意思,不是吗?马尔克斯在乔伊斯那里发现的自由和他从乔伊斯和福克纳那里学到的结构和技巧等经验又通过这个哥伦比亚人作品的翻译被传递给年轻一代英语小说家。如果没有机会接触翻译作品,这种令大作家超越单一语言和文学传统限制来发挥作者威力的发现的革新过程将是不可能的。其实,翻译是具有强大的说服力,通过让作家进入民族文学或单一语言传统之外的文学世界来拓宽和加深他对风格、技巧和结构的认识。就好像画家和音乐家那样,作家之间相互学习技巧,完全不是对影响的恐惧和焦虑。
直接当学徒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当然,除了正规学校环境(如创造性写作、函授课程或工作坊等)外,艺术家可以用其他方式寻找导师。青年作家能够从其他地方得到的书越多,创造性影响的潜在流动就越大,激发文学想象力的火星就越发不可抗拒。通过多语言的创造,翻译在扩展文学地平线的过程中发挥了可模仿的、根本性的重要作用。世界范围的作家共同体如果没有翻译是不可想象的。
歌德相信,如果文学把自己封闭起来,切断与其他文学的交往和联系的话,它就会陷入枯竭,文学的资源也将枯竭。不仅文学,连语言本身都会在与其他语言的接触和交流中发展壮大。新表达方式的语言融合的结果是词汇的扩张、感情的潜力和结构性实验。换句话说,伴随翻译而来的地平线延伸不仅影响某种语言的读者、说者、作者而且影响语言本身。
一门语言拥抱融合和吸收新元素和外国短语和说法越多,它作为表达媒介就变得更大、更有力、更灵活。设想一个无知的政府和排外的社会运动通过在国内禁止使用其他语言,首先创造某种语言的“纯洁性”然后竭力维持这种纯洁性的努力是多么令人悲哀啊。如果没有全世界跨文化的多语言的不可抗拒的、不可避免的、一波又一波内容丰富的交流,他们试图保存的语言将因为缺乏接触新的不熟悉的表达和交流手段而最终老化、腐蚀、衰弱下去。
原作者: 伊迪丝•格罗斯曼 吴万伟 译 来源:
同道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