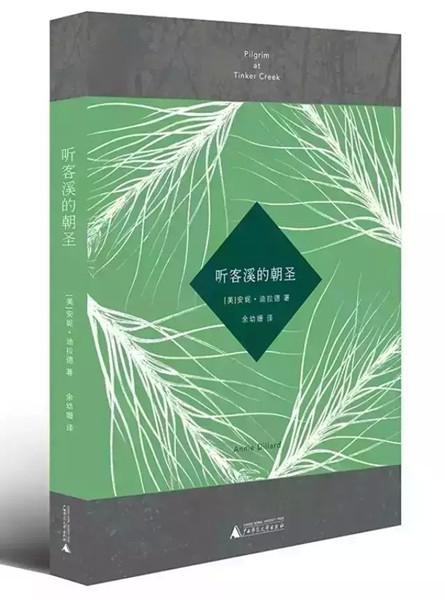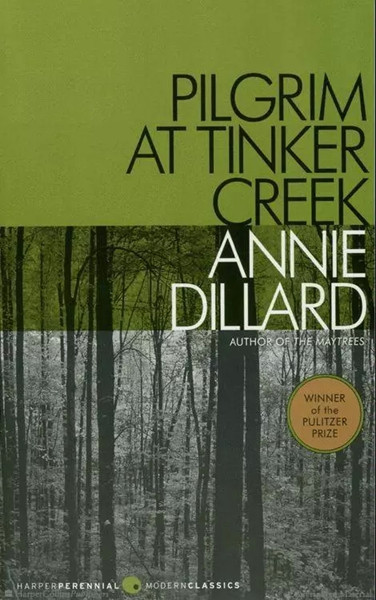1972年10月,22岁的安妮·迪拉德跟丈夫一道北行度假,在她的怂恿下,两人来到缅因的阿卡迪亚汽车营地野营。“没啥好玩的,”安妮在日记里写道,“我们整个10月都住那儿,住帐篷。我读书,读书,读书,跟以往一样。”
安妮写日记很勤,读书更多,根据她自己的记录,大学毕业两年来,她一共读了五十多本书,书作者不乏梭罗、爱默生这样的美国超验主义大师。梭罗写《瓦尔登湖》,世所闻名,爱默生是梭罗的朋友,虽然没写过什么大部头,留下的多是讲稿、演讲和随笔,也被尊为大师级的思想家,惠特曼等人的偶像,超验主义是给梭爱等人的一个宽泛归类,他们都推崇精神的至高无上,阐扬人与自然之间的精神对应。
然而,安妮的毕业论文却给《瓦尔登湖》提出了一系列批评,她认为,《瓦尔登湖》是一本“写一个湖的书”,梭罗写的是湖,而不是人们所传颂的“荒野生活”,他只看到了自然是什么样,却未看到它“可能”是什么样。
挑剔让美国人引以为傲的大贤人梭罗,安妮不简单。她是锐气而直爽的人,目光如炬,善于发现问题。在帐篷里读的书中,有一本《北部农庄》,记录了作者亨利·贝斯顿在缅因州务农的经过,安妮从中读出了和梭罗一样的问题,那就是因缺乏想象力而呆板,对“可能性”不敏感,人只是生硬地观察和贴近自然,但那不能算是“wildlife”。爱默生有名言:“世界的存在,是为了教育每一个人”,意思并非人要低头附耳,听世界的教诲;爱默生想说,人应以人的视角来体验世界——尤其是自然。
1987年的安妮·迪拉德,已经有自己的小木屋了
贝斯顿的书,直接刺激了安妮写出《听客溪的朝圣》,称之为“自然文学经典”怕是有误导性,它跟《瓦尔登湖》、《寂静的春天》都不一样,也不同于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缪尔的《夏日走过山间》,可能更接近她引用过的蒂尔的“四季书”。《听客溪的朝圣》拥有梭罗,更不用说贝斯顿的书中缺失或不足的东西,也在一个更宽泛的意义上警示我们,为什么自己写出东西来那么乏味。
“阴影沿着高山嶙峋的两侧跳动;它们像根的尖端,像泼翻得水滩一般拉长,越来越急。暖暖的紫色素聚集在石头的每一道皱褶里,颜色加深并散开,凿出罅缝、深沟。那紫颜色一面跳跃并滑动……”
“阳光里有一种像肌肉的能量,与风中那精神能量相呼应……”
“只有孩童才听得见屋中公鼠的吟唱。只有孩童长大了双眼……”
“一杯池塘里的水看起来像是沸腾的汤。假如我把这杯水带回家,让污泥沉淀,微生物会自己分开来,然后我将它们分装在两只透明的碗里……”
译者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来翻译《听客溪的朝圣》,用词乃精细典雅,不避生僻。在安妮的笔下,没有一样东西不是活的,不仅溪边的蜻蜓、青蛙、螳螂、水虫是活的,水里的藻类,水上山间的风也是活的,乃至普照的阳光和岩石的阴影都是活的,会进会退,会跳动,会凝视,会收缩,会膨胀,有时稀薄,有时滞重。季节是人设的抽象概念,安妮写来都有质感,冬天感到“鞭打的空气”,夏末是“最饱满的时刻”,“绿意将一切隐藏”。
安妮是个收集素材的高手,也是狂人,素材,除了她在听客溪(这是她弗吉尼亚家乡山谷的一条溪)等地凭天赋加勤奋磨练的一双显微镜眼睛和巧手慧心收集的那些外,还包括各种其他人留下的文字。也许她与其他自然文学写作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她同等看重自然和书籍,而不倒向其中任何一方:倒向书籍的人难免掉书袋,如安妮所说:“我想要做的,并不是去学得这山谷中各种蓬勃生命的名称”;倒向自然的人,则多半只能写出一些充斥着一厢情愿的爱的文字来。
她读得多,看得便很清楚,自然写作基本分两类,一类是走过,看到,写下,如《北方农场》那种,另一类是非常艺术的,诗性的,甚至富有神学气息。这两类写作似乎彼此冲突,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但看微信的我们对优质写作的要求更低,基本上只求“有干货”了,我们浅薄至极地求实用,而那些缺少干货的人只好拼命地攀附热点,引用热词,什么流行就跟着玩什么。
给面目可憎的阅读者读《听客溪的朝圣》,犹如给看A片的人播巴赫的交响乐,绝对是种羞辱。书里的每段文字都像是鼓足了风帆,腿在走,眼在看,神在漫游,眼耳鼻舌,两手两足,甚至第六感也同时开启。两类文字在这本书里是一体的,水乳交融,诗的气息兜起了所有“干货”,间或,安妮还插入一两句人类学家式的性情之语。“朝圣”当然是趋神性的,可是实际上,书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与其说是摩顶放踵、庄严受洗的味道,不如说是一种孩子一样全面开放的心智。“我们正在远足,举行野餐,”她在一处写道,轻松随意,“像小狗般给养得肥肥胖胖,为的是那一死。我要不要再这树干上刻下名字呢?要是我摔倒在树林里呢?有没有树会听见?”
后来,《听客溪的朝圣》夺得普利策奖后,痴情的读者想象着,安妮怎样在膝盖上摊一本笔记本,席地坐于湿漉漉的木石之间,在鸟啭蛙鸣之间写下一行行字。他们都错了,安妮是在图书馆里写书的——必须远离家门,家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很不友好。人间没有绝对浪漫的事情,安妮在开始动笔时,早已不是梭罗那样的孤独漫游者,她在日记里表达了不安:一个家庭妇女写的书,有人会当回事吗?
孩童张大了双眼;读者郑重地读;所有的树——都听见了安妮·迪拉德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