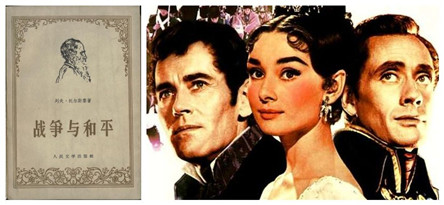他的灰发厚密如巢,一副特别宽阔的下颌,浅茶色眼镜,脸上的肌肉走向表示它们曾经紧绷过。他有一个我特难忘的画面:第一次见他时,他把我送出来,指了一个车站的方向,我走了没几步,就听他在身后高声喊我。我转身,只见他大步往我这里跑来,跑中还带着有弹性的跳跃,以减缓膝盖的压力。“我还是带你去车站吧,”他说。
哲学
2009年夏天,娄自良先生77岁,一米八三的身高一公分都没掉。我带着一本《温柔的幻影》去找他,在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几个中译本里,这个1991年左右出版的小册子是我读过最好的一本,不仅文字典雅有韵,而且,我将它与苏杭先生所译的《致一百年后的你》比较,两书中有交集的那几首诗,两人对原文的理解几乎完全一致,说明其准确性应该相当高。我见到娄先生,将这本书拿出来,看到他犹疑半晌的表情,才知道他早就忘了自己名下还有过这么一本东西。它是娄自良第一次 正式“试笔”俄语文学翻译,上世纪80年代的多数时间,他一直在出版社里从事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的编译工作。
于是我问他,这工作是不是很无聊?现在有谁还要看国产的大百科?何况还是……哲学?80年代的文化人的确热衷于引介西方哲学,不过那些有的还打着“内部参考”字样的书,或者一些二手货,看起来真的十分寒碜。
他笑而不答,转身从身后的书架上拿了本旧书给我:黑格尔的《小逻辑》。他的手脚有些慢,说话总是把每个字的语音拉得很长,因为身躯高大,在墙钟前移过时,钟的嘀嗒声都会忽而一轻。翻开那书,就能看到用圆珠笔做的细密的批注渗透在空白的页边和行间。“出狱后我40岁,之后我在工地上干活,白天挖防空洞,晚上就在读这本黑格尔,还有康德。”他说。
我推算了下,他坐牢的时间是1969—1972年。
娄自良的“家庭成分”不好,用兰波《地狱一季》里的一个词汇叫“坏血统”,所以1958年左右,右派的帽子早早就给他戴上了。他说,贺麟翻译黑格尔时是地下党,东躲西藏,偷时间翻译,比起来,自己能安全地读贺麟的译书,真是很走运了。牢狱之灾过后,他需要对付的只是时间。(他的老相识,另一位我多次访问的老翻译家王智量(1927年出生),当右派的时间比他还长,父母双双饿馁而死。王老后来写了本小说《饥饿的山村》,很有些影响。)
一个40多岁的男人,上海的家全被抄光,寄宿在穷亲戚家里,一贫如洗,每天挥锹运泥,夜里回来读书——这就是1972年的娄自良。而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6年。
我访问过不少翻译家,他们说起那段时间情绪都不错,因为下乡、下放、进牛棚改造的时候都能找到几本书,甚至还能做些翻译。他们很以这一点为傲。文化使人高贵大气,诚如是也。娄自良比他们还苦些,坐牢的三年半期间,他是没有书可读的,只能看四本毛选和《解放日报》。“出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仅有的一点钱买了几十本书,其中就有黑格尔和康德,还有马恩列斯著作的俄文译本,现在还放在家里。而且,我的身份太危险,随便找外语书,生怕又被人告发,只能买这种书才安全。”所以他说,哲学救他于危机之中。
右派
娄自良成右派之后,刚刚被流放,就意识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流放地是新疆,因为他并没有什么过错被找出来,只是因为当时那个臭名昭著的“百分之五”的规定。
他当时在上海师范大学担任助教,历任教研室组长和主任,而且还在教研室里负责组织反右工作,待遇不错。他的落难,起因于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里的一句卷首题词,大意是“我们的土地是用马蹄来耕的”,意指战乱时期。但是反右风一刮,他的教研室有个人被抓了出来,罪名就是他把这句话给抄了一遍。“我那时是负责人,就写了个辩护信给组织,替他挡了一下。”他措辞委婉,并没直说这个罪名安得莫名其妙,结果组织上一查,说他成分不好,索性直接打他做右派了。
“按比例,必须有一个人做右派。比例是百分之五,超过这个比例就要控制在百分之五,要是你说你这里都是好人,一个都抓不出来,那也不行,你怎么的也要凑出百分之五来。为什么定这个比例?我想过,是因为每一个一百人的群体里,杀五只鸡正好,不多不少,刚好够形成一种舆论,又不会脱离控制,然后就万马齐喑了。这真是通过精心策划的,超过了百分之五,人们就要怀疑:我们这里这么多坏人?‘坏人’之间也会互相交流、互相同情,事情就不好办了。”
但娄自良并没太多把柄可抓,于是给他一个从轻发落。1960年,他被支到新疆教书。他那时的职称没变,还是助教。同去的有个讲师,俩人都是右派。可是谈起那位讲师,娄自良说:“他连自己的妻子都检举,妻子生气,就反检举他,结果两人离婚了。”
“有一天晚饭后,我们一起散步,我告诉他,今天我到镇上去买了两双袜子,本想买一双,结果售货员说他们就剩了两双,让我都买去吧。你说这有什么不正常的?结果第二天,我被支书叫去了,支书问:‘你昨天干吗去了?’我说:‘没干啥啊。’他说:‘你是不是到镇上买袜子了?’我说:‘是,我买袜子去了。’他说:‘你这算不算囤积居奇?’”
娄自良这才知道,当晚那个同事就去汇报他的动态了。尽管如此,后来那人跟他关系还是挺近。娄自良说:“交朋友别太苛求,我考虑着,以后同他交往稍微小心就行了,既然你知道他是这么一种人。而且我想,你做人又何必如此,你就不怕领导看不起你?——那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
辞职
我喜欢访问的老人家,大多有股沉潜的力量。他们谈到往事里的可傲之处时,不用怀疑他们在吹嘘什么。他们与往事平起平坐,往事里掀起的每一寸波澜都是他们自己真实的高度。娄自良最有魄力的一个决定,是他从新疆的学校辞职,回到了上海。连我都感到奇怪:都被流放了,不好好待在流放地,居然还敢辞职?后来他在上海遇上文革,蹲了大狱,就跟这次辞职大有关系。我问娄先生:“你怎么敢干这样的事情?”
他反问:“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回上海?我在这里连家都没有,我父亲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我把他送回安徽让我母亲照顾了。我回上海做什么?
为了泡图书馆——那时的上海图书馆有外文书库存,我要读那些书。但是,我这种身份可不行。我就想了个办法。我跑到华东师大去找一个朋友,我跟他说:‘现在图书馆里可以借阅外语书了,我能帮你办证,你只要写个盖公章的申请信就行,写文字都不必用水笔,铅笔就行。’他信我,就写了一张申请书,我拿着这张东西回家,小心地把铅笔字擦掉,换上我自己的内容,擦掉之后,那纸面不是起毛吗?我就改用毛笔写上字,免得被人看出来。”
娄自良的脑子好使,写好之后,他找了一个傍晚去图书馆,趁着馆员快下班时把申请递了进去。“他们干了一天,多累啊,光线又暗,看了看就草草地批了。接下去的8个月,我每天一早喝碗粥,就从暂住的五角场出门,跑到图书馆看书,中午图书馆关门,我就到对面邮局坐着,有时假装在那儿写信,坐到下午1点再回来。午饭我是不吃的,晚饭也是一碗粥。”
但日子只这样过,没有收入也不行。辞职回上海的娄自良什么也不是,就连找个单位干保安都不行。“结果,居委会给我联系到某个工厂去干活,翻钢砂,拎钢水,整天挥铁榔头,”娄自良说。8个月之后我才报上户口,这才干上了活,干了一两个月,他们看我还行,有劲,头脑也不错,也就放心了。于是,我的生活就此固定下来,白天劳动,晚上读从图书馆借出来的书,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被抓进牢里。”
那天,我想让他给《温柔的幻影》签名,他推拒了,说这是太古老、太不值一提的书。2009年,他重译的《战争与和平》还在做最后的修缮,他说,等那本书出了再给我签。
没有青春的青春
——娄自良先生记(中)
文武
娄自良身上有股妖气,有经常发功的人的那种神态。我一直怀疑他有什么养生秘法,能在健朗中加入某些有关灵智的东西。最近一次见他,他终于告诉我,他百分之七十五的人生都在练少林寺的易筋经。
这个日后从文之人,得了许多习武的好处。“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经常去两个地方:一个是白渡桥,那里有个基督教青年会,在那里练拳击;另一个是外滩的某栋楼,我在那里跟一个山东人的团体学武术。”但是,若不是抗战结束,生于上海的娄自良差点就回不来了,因为他那位敏感的父亲死活都不愿意在日占区过日子,于1940年辞了职,带着全家人回到了安徽农村大后方。那里抗日宣传声势震天,娄自良一度萌发了从军的愿望。
“回来读中学时,我13岁,才刚刚入学,国民党政府就来招收知识青年参加去缅甸的青年远征军。我都去报名了,招兵的人看看我说:‘你太小了,还是别来了吧。’”
但对军队的热忱,在他心里是落下根了的。他的家庭经济状况不佳,读到高二时,他就考虑要读可入军队编制的大学,而不是普通高校。他去报考华东军政大学,结果父亲不准,后来哈尔滨外国语大学到上海招生,他去报考并得以成功入学。那个大学原先是延安抗大的一个俄文队扩展而来,1950年时,校长是刘亚楼。
在他说来,当时哈外俄语训练的高度和专业度是后来的学校所无法企及的。“你问我的自信从哪里来?我跟你说,我们当时的有些课程,现在的学生都闻所未闻。例如,现在学外语,学语法就行了,但我们那时有‘历史语法’课,请了苏联专家来,讲授俄语语法的历史沿革——这是费了多大的力气。”
但培养外语人才,当时几乎完全用于备战。在哈外学了两三年,朝鲜战争开打,包括娄自良在内的一批俄语学生都被拉去前线当翻译。他记得,和他同去的女学生有许多当场就哭了,因为从没想到过工作居然如此繁累,而他们当时所掌握的外语用于实践又是如此之难。
“所以你看,我说我不会叛国,是有道理的。”娄自良说。
商海
之所以提起“叛国”,是因为娄自良有过叛国的可能——至少在其他人眼里是如此。我认识他之前,便有圈内人向我述说着他的传奇:他在俄罗斯做过几年生意,而俄罗斯,人所共知,在收买内线、招降纳叛方面一向处于全球领先水准。
我不知道太多内情,但看上去,苏联解体时,已年近花甲的娄自良拥有的人脉资源突然都活跃了起来。“我有一个俄罗斯合伙人,是个犹太人,从小在苏联长大。他当时到北京来,我的另一个朋友,是个女孩子,写信给我说,她已与这个俄罗斯商人谈妥,办一家贸易公司,而且希望中方的负责人由我来担任。”
仅仅是因为精通俄语,一个从未经过商、新近退休的出版社编辑就能在一家贸易公司独当一面?我十分怀疑,可是娄自良说,他的生意做得很大。
“给你举个例子,”他说,“我去西伯利亚,有很多前苏联退休将领都住在那里,他们看到我来,开口就跟我说:‘你要什么都行——机关枪、高射炮、导弹,尽管开口。’军火都能随便买卖——你不敢相信吧?可这就是俄罗斯。”
在出国之前,娄自良的一位校友,时任华师大副校长,刚从美国回来,带着香烟来看他。得知他不久就要去俄罗斯,这位老党员面色一沉,劝他别去,他说:“老兄,你当过右派,去了不会太平的,就算你帽子摘了,国家对你能放心吗?”
“但是我还是去了,我做好了思想准备。我告诉我的校友,我这个人,你说我会做什么坏事都有可能,但我不会叛国。万一那边真的有谁有这种意图流露,我知道我会立即拒绝。我绝不会幻想去接触什么机密,否则我不但要替自己的安全考虑,还得时时担心别人的安全:因为俄罗斯人来找我,本身就是机密嘛。”
娄自良有种脚正不怕鞋歪的自信:“你要是被克格勃收买,你还能企图身在曹营心在汉,做双面间谍?你不可能以个人之力对抗那个严密的组织,它会把你严密地控制起来,再说,我真做了双面间谍,恐怕还得不到本国的承认吧。”
他大笑,当右派的日子顷刻成了用于自嘲的谈资。在我想来:他真可以就差一点成了军火商,乃至差一点当了间谍的事添油加醋、大大吹嘘一番的,可惜他根本没把心思放在这上面过。
那位犹太裔合伙人是个研究所的研究员,因学而商,说起来中俄两国也是兄弟情深,中国文化人在90年代出现“下海”潮,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心里产生了“解体”的感觉。我问他,都做成了点什么生意?他说,主要是木材,还有有色金属、钢铁和俄罗斯的自然资源,以及大兴重工业年代留下的丰厚家底,让邻国的商人十分眼馋。
“我做成的一些生意,是从俄罗斯买钢管卖给东北的一些公司,不过后来中方有关付款以及提供工业产品之类的承诺没有履行,反而要求再买一批钢管,两次一并支付。这么一来,我就不愿给他们办了。他们另找俄语翻译来办此事,也没成,因为俄方听不懂那翻译的话。那时中国的对外贸易简直是无骗不买卖。这笔生意让俄方吃了亏,不过我的中介费是拿到的,所以我也就懒得再帮俄方去追究。”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经济低迷到了令人垂怜的地步。“他们国内的企业就盼着往外卖东西。”娄自良说。他讲了个亲身经历:“有一次我去远东耶尔库茨克的一个百货公司,店里灯火通明,服务员都穿着白褂子,货架上却空空如也,就一双男鞋,一双半筒靴,一条裤子,没了。我把那双靴子给买了,是乌克兰进口的。在苏联时期,俄国只做重工业,由卫星国给俄罗斯提供日用品、农产品之类的商品,所以卫星国独立之后,供应链就断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里的人管我买的这种靴子叫‘星期鞋’,只能穿一星期,鞋底就掉了。我去莫斯科修鞋,找了个人问,说修不好,还跟我说,全莫斯科没有人能修,你就放弃它吧。”娄自良说。
他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问题问他:“你在俄罗斯到处跑,用什么交通工具?”
“当然是飞机,特别是在西伯利亚,那么大的地方只能坐飞机,”他说。“我经商的两年半里,俄制飞机的空难事情没少发生,我自己都奇怪,居然一次都没让我碰上过,还真是遗憾呢。”
我想,或许找他去经商的人认为他即便坐飞机掉下来,也能活着爬出来吧。这个人的生命力至今尚且如此顽强,何况“年方”60岁的时候。他能文能武且能商,一介全才,舍弃任何一个领域都值得惋惜,却有20年的生命是虚度了的。熟悉了他的人生,我觉得,我再没有资格因一事无成而抱怨环境、机遇、小人作祟或是别的什么了。
娄先生拿出他在俄国的老照片给我看,其时60岁,但看起来不过40来岁的样子,或许可以推测,他可能在40来岁时已有了60岁的长相。在这段岁月里,他像是被石化了一样,从没年轻过,也不会再衰老。从俄国回来,他才开始慢慢地搞文学翻译,才开始找回过去的梦想。
“文字会永远流传的,读者是不会绝种的。我放弃了很多个人的爱好,比如武术,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年轻时我还学过小提琴,后来也放弃了,就为专心做一件事。至于是30岁,40岁,还是60岁后再做,这个不重要。青年时代,青春什么的,我是真没有过,不过,”他拿起一本书,那是他新接的一个翻译重活——俄文版《布罗茨基诗全集》,“没有就没有吧。”
凶险与温柔
——娄自良先生记(下)
帝国
1992年,娄自良平生第一次到俄罗斯,仅仅花了两个星期就办好了营业执照。在俄方的外资委员会登记,又拿到一个执照。那时俄方要求,公司要有至少3000万卢布的资金,娄自良一文也无,除了懂俄文,全赖俄方合伙人之力,这些事方才办妥。
“我真是见识到什么叫‘没落帝国’,”他说。“我去莫斯科的国民经济展览馆,那个豪华啊,原子能馆、汽车馆、导弹馆……广场当中就是一架图—154,一个喷泉,周围伫立着16座真人身高的女郎雕像,镀金的,代表俄罗斯和另外15个加盟共和国。我去的那天,蒙蒙细雨飘在天上,门口立着16根旗杆,现在只有俄罗斯那面旗还飘着——另15个国家都独立了。这真叫一片凄风苦雨。不过那16座雕像还在,后来还重新镀过。”
我常听娄自良讲俄罗斯的事。解体后的苏联社会失序,人心动荡,住在莫斯科时,他去黑市弄了一支枪放在寓所里。这支枪不是装子弹的,而是装麻醉剂,遇到匪徒时可以把对方击晕。不过出门时,他一般不带枪,有一次还被劫走了整整500美金。“我就是带着枪也没用,我被六个人围住了,只能舍财脱身。”他说。
其实在俄3年,凶险程度还不如在国内的时候。娄自良在上海师范大学任职时,臧克家的儿子臧乐安刚刚入党,积极性很高,跟他说起学校里搞大鸣大放,问他要不要也写点什么。娄自良说:“我不傻,我感到这里面有陷阱——不是说臧乐安要害我,大家都不知道将来可能出现些什么样的后果。但我想,我不说理论,讲一些事实,总可以吧。比如说,我反映干部分配问题。我在北京的俄语高级研究班毕业之后,北京来了一个调令,调我去那里工作,可我不知道这事,是我一个在人事处工作的朋友给我透露的,说是被领导压了下来,从来不提,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们当时研究班毕业的人很少,因此能毕业的人在全国的水平算是很高的了。但是你们为什么不让我知道这件事?”
他到西伯利亚,见识了冻土苦寒,仿佛重又回到了在西北的日子。之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做易中天《品三国》等系列畅销书的一位老编辑几次找他,请他写回忆录,特别回忆那段特殊的日子。娄自良笑道:“我人微言轻,还是做翻译最适合。”

在俄罗斯,他有些很堪回味的经历,和《真理报》主编的交往便是其中之一。“《真理报》,”我问娄先生,“到90年代早就名声败坏了吧?”他说:“可能是这样,但是办报的仍然是知识精英,主编是德高望重的人。”
在上海时,俄罗斯的哲学研究所代表团来访,住在锦江饭店。娄自良认识了带团的人,他到俄罗斯时,就去他的单位回访。娄自良回忆说:“那天研究所里有个老先生坐着,我不知道他是谁,我要走时,他们说今天是老先生生日,有个晚宴,你别走了。赴宴之后,老先生特地找我说话,他笑逐颜开,说:‘我见的人多了,我觉得你是个可交的人。’”
“那会儿我才知道他是《真理报》主编。那天老先生给我个纸条,邀请我星期天到他家参加私人性质的家宴,我就去了。摁响门铃之后,他的夫人来开门,脸上很惶惑的样子,好像不太高兴。她问我找谁,有什么事,我说,我来参加某某某的生日宴会——俄国人名字太长,我现在记不住了。见到老先生后,他也一副埋怨的样子:‘你怎么晚来啦?宴会是昨天呐。’”
“我把纸条拿给他看,他这才知道自己写错了。这时候他的夫人立刻就怪罪上了:‘你真是的,老糊涂啦,自己生日的时间都搞不清——口吻跟中国的老太太都一样。’这主编就跟我说,连带着安抚她的情绪:‘她是个很好很好的女人……。’”娄自良说。
“我们谈了很多,但我们似乎有默契,绝口不谈政治。他在《真理报》干了20年,后期当上了主编。他不怎么说自己干这个职位的事,也不提知识精英什么的,他最骄傲的事,是自己曾是个舢板运动员。我们谈到深夜,他夫人一直把我送到地铁站,顺带遛一条小狗。我拥抱了她。”
后来娄自良还见了他一次。“因为那次晚宴没吃成,后来我给他打电话邀请他到莫斯科的北京饭店吃饭。他说:‘我能带夫人一起来吗?’我说:‘对不起,我失礼了,应该请您夫人一道来的。’过一会儿,他又来个电话:‘我女儿能来吗?她在警局工作。’于是女儿也来了,女儿一来,女婿还能落下?也跟来了。又过了一会儿他又来电话:‘我儿子能来吗?他有辆车,可以送我。’你看,我就喜欢俄罗斯知识分子这种质朴纯真,中国人好像不会这样,就是这样想,也不敢说出来,生怕被人瞧不起。”
这位主编后来得了喉癌,娄自良去他家看他,他妻子说很快就会出院。没想到不久,他就传出了死讯,说是出了医疗事故,护士打错了针。几年以后,娄自良有次从莫斯科到远东去,火车上上来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青年女子,带着锅碗瓢盆。他跟她们说了会儿话,原来他们都是军属,提着一大堆家什去东边与戍边的亲人会合,还知道不少内幕。聊到那位主编的事情时,两个女人一下子变了脸色,压低了声音,说这里面肯定有政治阴谋,医疗事故只是个借口。
“这件事让我一下子感觉到俄罗斯的某些传统仍在,而且扎根很深,”他说。“我读过那主编的最后一本书,观点与此前大大不同,不像《真理报》在职时那么主流了。他虽然退休,在俄罗斯影响力还是很大,存心要算计他的人,是有动机的。”
女孩
我注意到,娄自良爱说“女孩”,他管那位介绍他去经商的中间人叫“女孩”,管车上的俄罗斯军属叫“女孩子”。他说话很慢,后边那个“子”字我就听得更清楚。看一个人对他人的称谓,就可以判断他大概是怎样的人。向自己的朋友提起一位自己认识的年轻女性,说“我认识个女的”和“我认识个女孩”,是大不一样的。
“我受了这么多波折,不过我对人还有爱,至少在俄罗斯是这样,”他说。“有一次我遇到一位修女,站在路边,立着个牌子说‘给孤儿募捐’。我就给了她一点钱,走开后,就听那女子在背后叫我:‘上帝会保佑你的——’这话修女大概一天会说很多次吧,可我听那声音特别诚恳,就忍不住回头看了她一眼:原来她在向我招手呢,还喊:‘上帝爱你!你来,你来,你向上帝祈祷一下,上帝他一定会保佑你的!’我发现她站在一个教堂对面,我就过去,也站到那里,祈祷。我还问她:‘你们画十字,是从左画到右,还是从右画到左。’”
娄自良不信教,“我只是做给她看的。可是,这个修女那么诚心诚意,恭恭敬敬,我真的很受感动。”
娄自良家有3个孩子,70年代,就在他寄寒篱下、每日戴着安全盔在工地上拎钢水的日子里,长女和次女都还在读小学。学校的人来找他,问是否要减免学费,因为他家太困难了。他说不用,他不想给孩子带来心理阴影。
1976年,娄自良44岁,仍然在干体力劳动,第三个孩子又在母亲腹中了。那时计划生育已经开始,妻子问他:“看来这下不能要了,打吗?”娄自良说:“绝不打。”
“我不想失去第三个孩子。那时还有一对夫妇,丈夫是导演,妻子是演员,想要收养这个孩子,我都拒绝了。我说,不管孩子被收养后的生活多美满,她都会有被遗弃感。那时我的妻子也在工地,每天要搬重物,那么这事怎么办好呢?我教了她个办法:我告诉她,你一使劲,就佯装腰痛,跌坐在地下。腰痛这种症状,医院是查不出病因的,但又没法让你继续干,你就可以休养几个月,到时就是人家想给你打也不行了,只好让你生下来。”
结果又是个女孩。孩子长到两岁,娄自良摘去了帽子,进了译文出版社,从房顶晚上有尿滴落下来的陋室搬进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新房。他的老友,《蒲宁文集》、《金玫瑰》、《骑兵军》的译者戴骢,同他是邻居,后来戴骢着手编丛书,才找了娄自良试笔翻译。20年的动荡期里,娄自良俄语没丢,学习未曾稍怠,到底是给他找到了稳定的饭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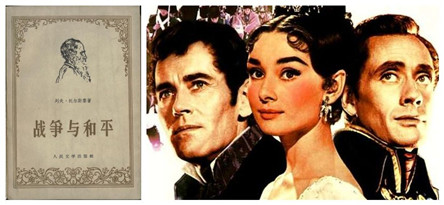
这种隐忍蛰伏、一朝奋起的老套故事,世上从来不缺。之所以记下来,是因为娄先生有太多“神人”的禀赋,即便以语言勉力传递,也仅能记其十一。他译的《战争与和平》,识货的人自然能鉴别出胜于旧译本的地方,兹不赘言。我时常想:自己认识太多这样的人,是不是也表明了命运所予的不凡的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