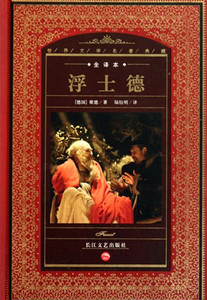从《浮士德》的翻译实践中,作者获得了一些感悟,分别涉及诗歌翻译的三个问题:一是译诗的一种境界;二是译作与原作的关系;三是诗歌翻译的创造性问题。作者认为:大智若愚,不留痕迹,为诗歌翻译中一种难以企及的境界;译作与原作的关系应为似与不似,追求面面俱到必然得不偿失;诗歌翻译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在诗歌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意志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这种主体意志中,活跃着一种宝贵的创造性精神。
我翻译的《浮士德》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后,至今一直畅销,一版再版,现在即将由花城出版社再出新版。我的译本出版后,得到了不少读者的赞誉,也得到了不少批评。同时,我也不断收到来自各方面的询问,其中包括两位德语文学博士的询问,她们要进行译文版本的比较研究,问我依据何版本进行翻译及翻译的原则问题。对读者的溢美之词,我受宠若惊;对读者的批评,我深刻反省; 对读者的询问我想在此一一作答。我依据的版本为Berlin und Weimar, 1965年版。在翻译悲剧第一部的时候,我还参照了美国班塔姆名著丛书1985年的《浮士德》德英对照版。同时,我还参照了三个著名的中译本,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董问樵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钱春绮译本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绿原译本。尽管我的译本体现了我的个性特征,体现了我译文语言的风格与力量,但我要感谢以上翻译名家给我的启发和滋养。董问樵的挥洒自如,才华横溢,钱春绮的严谨老道,绿原的既严谨又流畅的散文翻译都是我汲取营养的源泉。至于翻译的原则问题,《浮士德》是一部诗剧,除了少数对话外,大部分对话与独白,都是以诗的形式写成,因此,我在翻译的时候是把它当作诗来翻译的。通过《浮士德》的翻译,我获得了一些感悟,愿意拿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也算是我翻译《浮士德》的一些参考原则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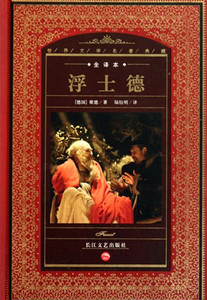
《浮士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 陆钰明译)
感悟一:大智若愚乃译诗的一种境界
著名作家巴金曾说过一句话: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如果把诗歌翻译看作是一门艺术,那么,这句话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诗歌翻译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
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余振先生是一位俄罗斯文学翻译专家,他翻译的《莱蒙托夫诗选》在上个世纪风行全国,出版了一百七十多万册。他译的普希金、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不断被各种版本的诗集所收录、转载。我曾经向他打探译诗的秘诀,他笑而不言,却让我看看他送我的《普希金长诗选》中的译后记。于是,我发现了如下几句话:“为了忠实于原文的内容,我主张大家一致反对的‘逐字逐句地直译’,万不得已时可以酌量采用意译,以补直译之不足。因为我们看到的原文是由字组成句、由句组成诗的,丢开了‘字’和‘句’而从字外行间去找‘神’,老实说,我没有这种本领。限于自己的能力,只好‘逐字逐句地直译’”(余振,1984:392)。 我当时没有把它看作是译诗的秘诀,而是导师的一种谦逊。
导师的译诗主张据说源自梁宗岱。梁宗岱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译著《一切的峰顶》的序中说,他“不独一行一行地译,并且一字一字地译”,“这译法也许太笨拙了。但是我有一种暗昧的信仰,其实可以说迷信:以为原作的字句和次序,就是说,经过大诗人选定的字句和次序是至善至美的。如果译者能够找到适当对照的字眼和成语,除了少数文法上地道的构造,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移植过来。我用西文译中诗是这样,用中文译西诗也是这样。有时觉得反而比较能够传达原作的气韵”(海岸,2007:74)。
我不懂俄文,无法体会导师译文的妙处。但梁宗岱的译文我是拜读过的,他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可谓登峰造极,至今无出其右者,我佩服之至。经过多年的诗歌翻译实践,我终于明白了。他们的译诗主张其实道出了一种难以企及的境界,这种境界便是:大智若愚,不留痕迹。跟巴金所谓的无技巧是一致的。所谓大智,便是对原文的透彻了解,是译者与作者的心灵感应,也就是郭沫若在《雪莱诗选》序中所说的那样:“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我爱雪莱、我能感听得他的心声,我能和他共鸣,我和他结婚了。---我和他合而为一了。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的一样”(罗新璋,2009: 405)。所谓若愚,即是以朴素的、一种酷似原文的浑然天成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我虽然还没有达到,但我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目标来追求。在译《浮士德》的时候,我确实想追求这样一种目标,在译到浮士德面对现实的郁闷、向往自然的清纯的一些内心独白的片段时,我确实感受到了浮士德内心情感的起伏,他的忧郁,他的理想,他的向往。我感到我和他产生了共鸣。但我是否能以一种朴素的、浑然天成的方式呈现出来,却不得而知,我希望得到读者们的指点。下面是悲剧第一部中《夜》的一段浮士德的内心独白,从中可以看出我对译文的追求。
原文:
O sähst du, voller Mondenschein,
Zum letztenmal auf meine Pein,
Den ich so manche Mitternacht
An diesem Pult herangewacht:
Dann über Büchern und Papier,
Trübsel’ger Freund, erschienst du mir!
Ach! Könnt’ ich doch auf Bergeshöhn
In deinem lieben Lichte gehn,
Um Bergeshöhle mit Geistern schweben,
Auf Wiesen in deinem Dämmer weben,
Von allem Wissensqualm entladen,
In deinem Tau gesund mich baden!
我的译文:
啊,温柔的月光,我多么希望,
你最后一次见我痛苦悲伤,
多少次我坐在这书案前
深夜不眠,等待你的出现:
忧郁的朋友,你终于光临,
在这些书籍和纸张间留停!
啊,但愿我能沐浴你的柔光,
漫步于山峰之上,
在山洞周围跟精灵们轻舞,
在你的清辉中在草地上漫步,
驱除一切知识的迷雾,
彻底沐浴于你的清露。
我想努力以一种朴素自然的现代汉语来译原文朴素自然的德语,以两行一韵的方式来译原文的两行一韵的表达方式。只是在节奏上个别地方略显参差(如第八行译文用了较少的文字来译,显得音顿上有些缺失),但为了保持行文的流畅与自然,我没有像有的译者那样去凑字来达到节奏上的齐整。我这译法是否合适,有待于读者们的指点。我想追求一种大智若愚的境界,我努力保持不增不减,几乎逐字直译,希望在不损伤译文语言的前提下,极力保持原文的艺术特征。
感悟二:似与不似
大智若愚体现了诗歌翻译中的一种境界,但这种境界有时很难企及,译者不得不在他的译文中对原作进行一定的改动,以调适译文的结构与表达。这种改动是必须的,也是不得不作出的,这样一来,便引出了诗歌翻译中的另一个问题,即译作与原作的关系问题,我认为那便是:似与不似。
意大利有句谚语:翻译者即叛逆者。
几乎所有的译者都希望自己的译作与原作相似,或与原作产生类似的艺术效果。所谓的形似,神似,追求的都是似。但也不尽然,有的翻译家希望自己的译作能与原作抗争、竞赛,甚至超越原作,这种不凡的气派令人钦佩。
最早提出译作与原作竞赛的也许是古罗马翻译家昆提利安(M. F. Quintilianus, 35-96), 昆提利安是古罗马早期继西塞罗、贺拉斯之后杰出的演说家、修辞学家和翻译家,他说:“我希望我们的翻译并不仅仅是释义,而是在表达同一意义的前提下与原作抗争和竞赛” (Since I would not have our paraphrase to be a mere interpretation, but an effort to vie with and rival our original in the expression of the same thoughts. Robinson, 1997: 20)。
本雅明认为译作是原作的来世:“译作因为原作而产生------然而却不是原作的现世,而是原作的来世。”说明译作并不等同于原作,或者不是原作的翻版。他反对译作模仿原作,“假定译作的本质是竭力追求与原作相似,那就根本不会有什么译作存在了。因为原作在其来世里应当已经经历了变化,否则,不经过蜕变与再生,我们也不会称其为‘来世’。”(谢天振,2008: 322-324)。这种观点与意大利的谚语是相一致的。
译作与原作的关系,我认为就在似与不似之间。译作保持与原作某种程度的相似是毋庸置疑的。译作从原作中脱胎而来,带着原作的血缘关系,从而带着原作的种种遗传因子。译作相似于原作是不言而喻的,否则便不能称其为译作。但译作并不等同于原作,或者说译作与原作并不百分之百地相似,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一种语言被转变为另一种语言,其所带的文化被另一种文化所替代,并且又加上了译者这一可变性因素,再严谨的译作也不可能等同于原作了。
似与不似这一对矛盾在诗歌翻译中尤为突出。因为诗歌是一种高度精炼的语言艺术,一种语言所写的诗歌,其固有的音、形、义构成的审美效果到了另一种语言中可能荡然无存,或者支离破碎,需要经过诗歌译者的小心修补或者创造性移植。在翻译《浮士德》的时候,有时我会对原文的用韵作出适当的调整(比如原文abab韵式我会变成aabb韵式),有时会对原作的诗行作出适当的调整(比如为了行文的需要,有时我会对原诗上一行与下一行进行对调),但这种调整,不是随意为之,而是由于我作为一个译者在能力有限时迫不得已的偶然为之。这种调整在整个译文中所占的比例很小。比如在译悲剧第一部“瓦尔普吉斯之夜之梦”这一段插曲中的几段台词时,我把原文的abab韵式改成了aabb韵式:
原文:
Purist: Ach! Mein Unglück führt mich her:
Wie wird nicht hier geludert!
Und von dem ganzen Hexenheer
Sind zweie nur gepudert.
Junge Hexe: Der Puder ist so wie der Rock
Für alt’ und graue Weibchen;
Drum sitz’ ich nacht auf meinem Bock
Und zeig’ ein derbes Leibchen.
Matrone: Wir haben zu viel Lebensart,
Um hier mit euch zu maulen;
Doch, hoff’ ich, solt ihr jung und zart,
So wie ihr seid, verfaulen.
我的译文:
纯粹主义者:唉!我何不幸来此地:
声色绮靡无正气!
纵观整个女魔伦,
只有两个脸扑粉。
年轻女巫: 脸上脂粉如衣裙,
只合白发老妇们;
我骑山羊裸身体,
显露肉体有生气。
中年妇女: 我们文明有分寸,
不和你们口舌争;
你们年轻又娇嫩,
但愿不久就凋零!
这段译文虽然韵式跟原文不一样,但原文用韵,且四行诗中用两个韵这一事实我在译文中得以保存,只不过韵的排列有所变动,而原文的意义则丝毫没有变,这也算与原文保持了似与不似。从审美的角度来说,这可以称作审美转移。
感悟三:诗歌翻译是一种创造
当一位译者在诗歌翻译中被迫对译作进行一番改动,以达到跟原作的异曲同工之妙,这时译者的劳动中便融入了一种创造性精神。他的劳动便是一种潜在的创造。而如果这位译者对译作的改动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或者说是故意的,那么,这位译者的劳动,便是一种明显的创造。这样的例子,应该说,在古今中外的翻译史上不难找到。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菲兹吉拉德(Edward Fitzgerald)翻译波斯诗人莪墨(Omar Khayyam)的《鲁拜集》(Rubaiyat)便是明显的一例。
关于诗歌翻译的这种创造性特征,在一些著名的诗歌翻译家的论述中可以找到。如在前面所引的郭沫若在《雪莱诗选》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的一样”。而余光中在《翻译与创作》一文中则说得更清楚:“可是翻译,我是指文学性质的,尤其是诗的翻译,不折不扣是一门艺术。……真有灵感的译文,像投胎重生的灵魂一般,令人觉得是一种‘再创造’”(海岸,2007:427)。
如果把诗歌翻译看作是一门艺术,那么,其创造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艺术中,那种光芒四射、震慑人心的力量皆来自独创。但诗歌翻译并不完全是艺术,它一半是艺术,一半是科学。科学求真,艺术求美。因此,诗歌翻译总是在求真的基础上求美,并且总是在求真与求美的两难境地中痛苦前行。而一位诗歌翻译家总是在人们的责难声中完成其崇高的使命:求真的批评家指责其不忠,求美的批评家指责其缺乏独创。
在翻译《浮士德》的时候,我也总是在求真与求美的两难境地中痛苦前行。有时为了渲染气氛,有时为了再现人物特征,有时为了增强情感色彩等,我会对原文作出适当调整。比如在翻译悲剧第二部第一幕《宽敞的大厅》中一位醉汉的台词时我作了一些调整:
原文:
Sei mir heutte nichts zuwider!
Fühle mich so frank und frei;
Frische Lust und heitre Lieder,
Holt ich selbst sie doch herbei.
Und so trink ich! Trinke, trinke!
Stoβet an, ihr! Tinke, Tinke!
Du dorthinten, komm heran!
Stoβet an, so ist’s getan.
Schrie mein Weibchen doch entrüstet,
Rümpfte diesem bunten Rock
Und, wie sehr ich mich gebrüstet,
Schalt mich einen Maskenstock.
Doch ich trinke! Trinke, trinke!
Angeklungen! Tinke, Tinke!
Maskenstöcke, Stoβet an!
Wenn es klingt, so ist’s getan.
Saget nicht, daβ ich verirrt bin,
Bin ich doch, wo mir’s behagt.
Borgt der Wirt nicht, borgt die Wirtin,
Und am Ende borgt die Magd.
Immer trink ich! Trinke, trinke!
Auf, ihr andern! Tinke, Tinke!
Jeder jedem! So fortan!
Dünkt mich’s doch, es sei getan.
我的译文:
今天千万别惹我!
我觉得自由又自在;
新鲜的喜悦快乐的歌,
全是我自己带过来。
我要喝酒!饮,饮,饮!
大家碰杯!叮,叮,叮!
你请出来,后面那位!
咱们碰杯,这样才对。
我的老婆破口骂,
对着皱衣撇嘴巴,
随我怎样夸自己,
骂我是个穿衣架。
我还要喝!饮,饮,饮!
碰起杯子!叮,叮,叮!
穿衣架子,来碰杯!
杯子碰响,这样才对。
不要说我迷迷糊糊,
我在这里舒舒服服,
老板不欠账,可求老板娘,
最后还可求侍女来帮忙。
我只管喝酒,饮,饮,饮!
大家伙碰杯,叮,叮,叮!
大家碰杯,继续碰杯!
我还认为,这样才对。
原文三段台词结构相似,押韵的方式完全一致:a b a b c c d d。三段台词中除了前面四行诗各不相同外,后面四行在各段中几乎相似。在各段中完全重复的只有第五、第六行的四个词:Trinke, trinke! Tinke, Tinke!(喝啊,喝啊!叮当,叮当!),这四个词充分体现了醉汉嗜酒如命的特点以及喝酒后的醉态,所以在三段台词中得到了完全的重复,以增强其艺术效果。同时,这四个词又正好处于诗行的末尾,押相同的韵。从词的构造来看,两个词几乎完全相同,都是双音节词,只是在trinke一词中多了一个辅音字母r,要是从醉鬼的嘴里说出来,发音含糊一点,根本听不出有什么区别。这给翻译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为了体现原文夸张的艺术效果,我用“饮,饮,饮!”、“叮、叮、叮!”来翻译这两个词。原文两个双音节词我用三个单音节词来翻译,从声音系统来考虑,原文只有些微差别的辅音r,我用略有不同的声母来译,韵母则保持一致。而三个单音节词的重复对表现醉汉的醉态起到了渲染的作用。单音节词的简单重复正好描写了醉汉发音艰难、含混不清的特征。
另外,从押韵方式来看,原文三段台词为a b a b c c d d的韵式,我的译文第一段保持跟原文完全一致的方式,第二、第三段则略有改动,但整体上仍保持相似的韵律。我曾想完全保持原文的韵式,但这样束缚自己后,发现我的译文受到了损伤,失去了译文语言应有的光泽和生气。于是我略作改动,以自然、生动为界限,即在确保译文语言自然、生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传达原作的艺术特色。整个《浮士德》的翻译我都以此为原则。原文不押韵的(如海伦的对话与独白,她代表了古希腊诗歌艺术,说话不押韵),我也不押韵;原文用韵的,我也用韵;原文用什么方式的韵,我也用什么方式的韵。但有时不能完全做到,一旦译文语言受到了损伤,我便略作改动,以确保译文语言的自然、流畅。在诗歌翻译中,有时求真必须让位于求美,模仿必须让位于创造。
如果把诗歌翻译当作是一门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它也确实是一门艺术,那么,一位诗歌译者便是一位艺术家,他必须拥有艺术家的才华与天赋,否则,他的工作必将是失败。他的工作中必须饱含着一种创造性精神。在诗歌翻译中,这种创造性精神是随处可见的:译者对全局的运筹帷幄,对细节的小心修改,一行诗的排列,一个韵脚的修正,一个字的替换,甚至一条注释的增加,对词语意义的揣摩,是把原文意义直陈出来,还是以迂回曲折的方式表达出来而给读者留出想象的空间……,所有这一切,都浸透着一个诗歌译者的心血、品味、才华与创造精神。
总之,在诗歌翻译的过程中,对原作的理解,依赖于译者的审美体验、对原语语言和文化的掌握程度、艺术的敏感性等因素;而要以一个合适的形式表达译作时,又依赖于译者的美学趣味、对语言的掌控能力、翻译策略等诸种因素。一句话,在诗歌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意志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这种主体意志中,活跃着一种宝贵的创造性精神。
参考文献
1,本雅明. 译者的任务[A]. 见谢天振. 当代国外翻译理论[C].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2,郭沫若. 《雪莱诗选》小序[A]. 见罗新璋、陈应年. 翻译论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梁宗岱. 译诗集《一切的峰顶》序[A]. 见海岸. 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4,余光中. 翻译和创作[A]. 见海岸. 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5,余振. 普希金长诗选[M]. 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
6,Robinson, Douglas.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作者简介
陆钰明,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翻译学、诗歌翻译,已出版专著、编著、译著二十多部,发表论文二十多篇。